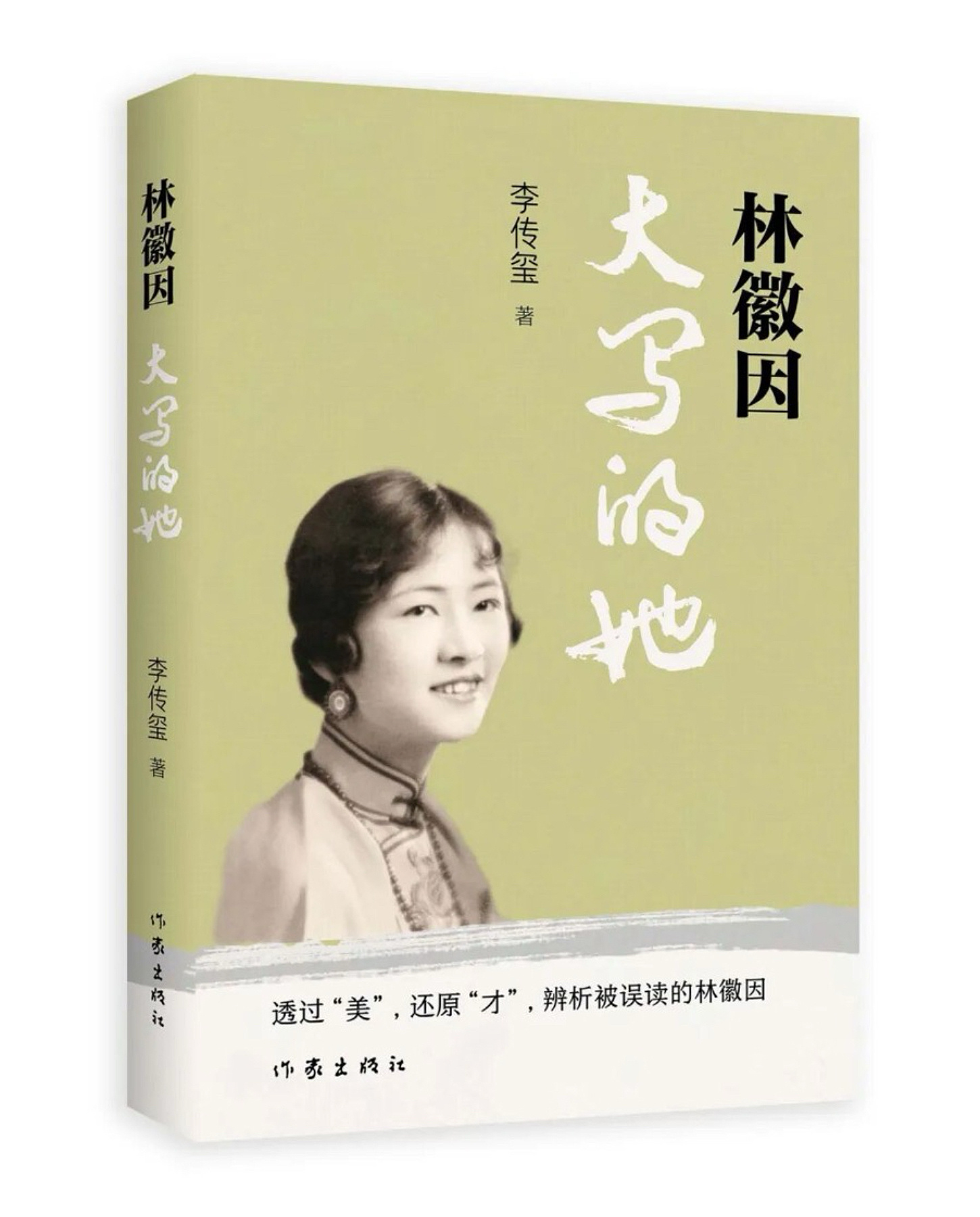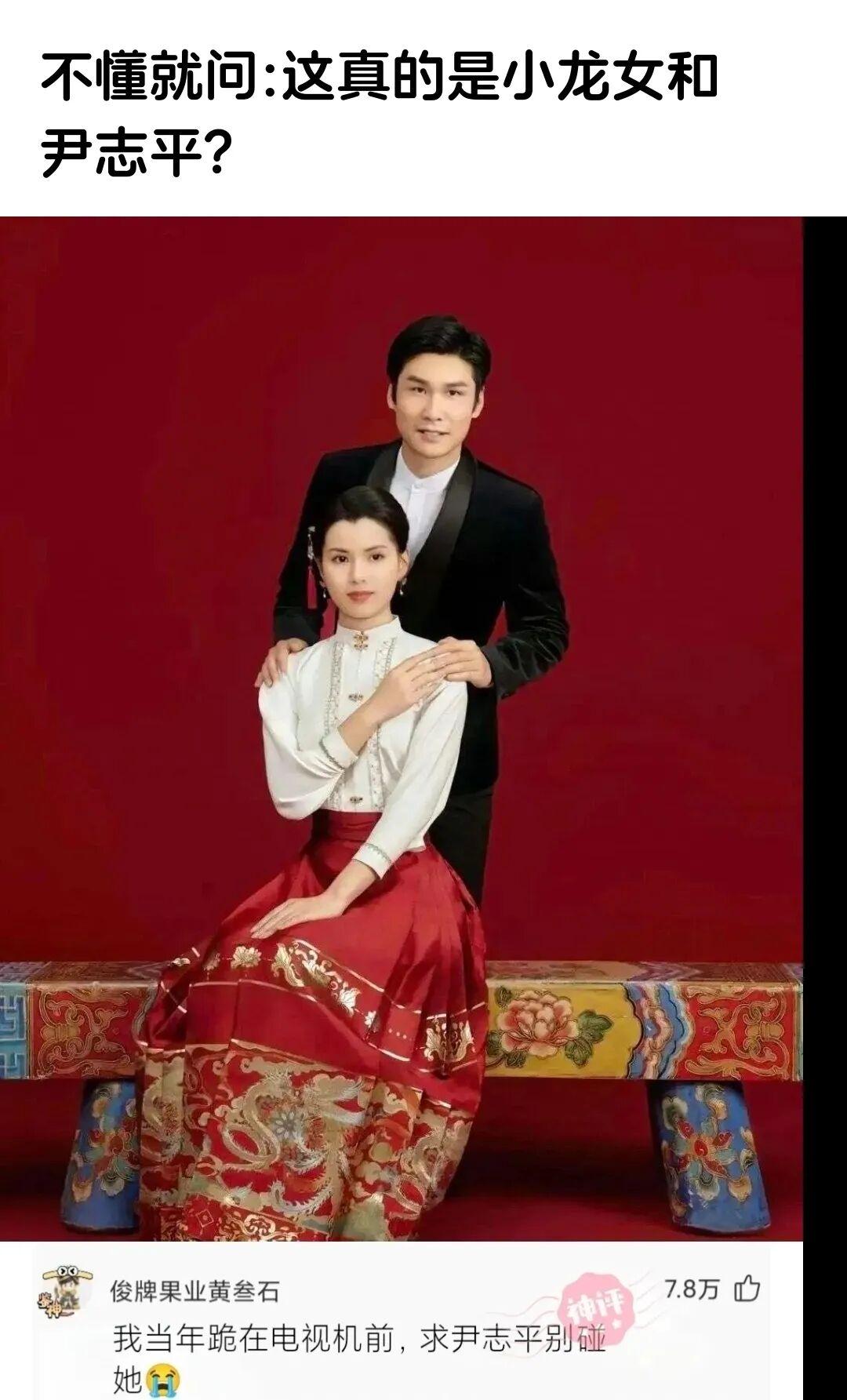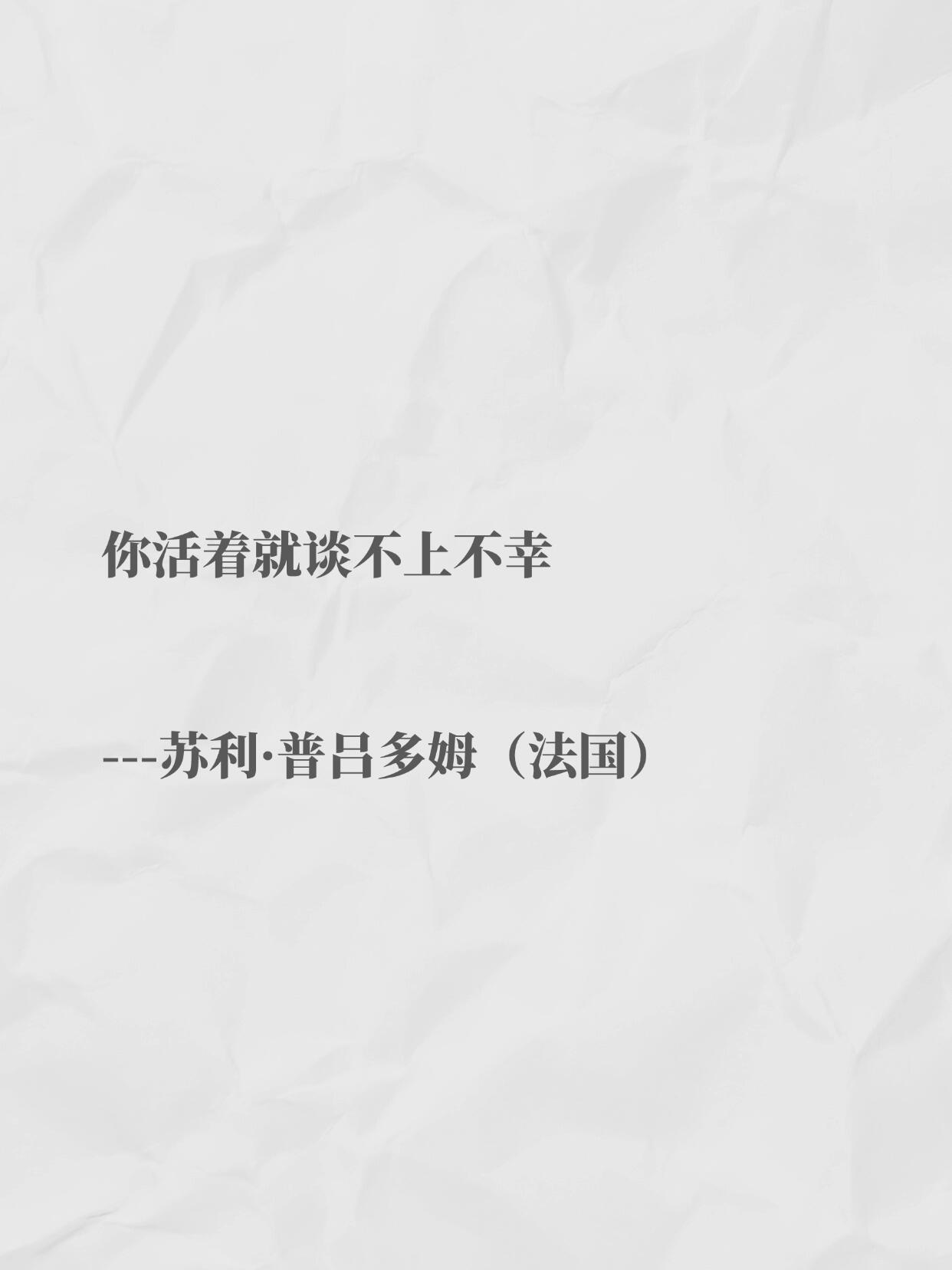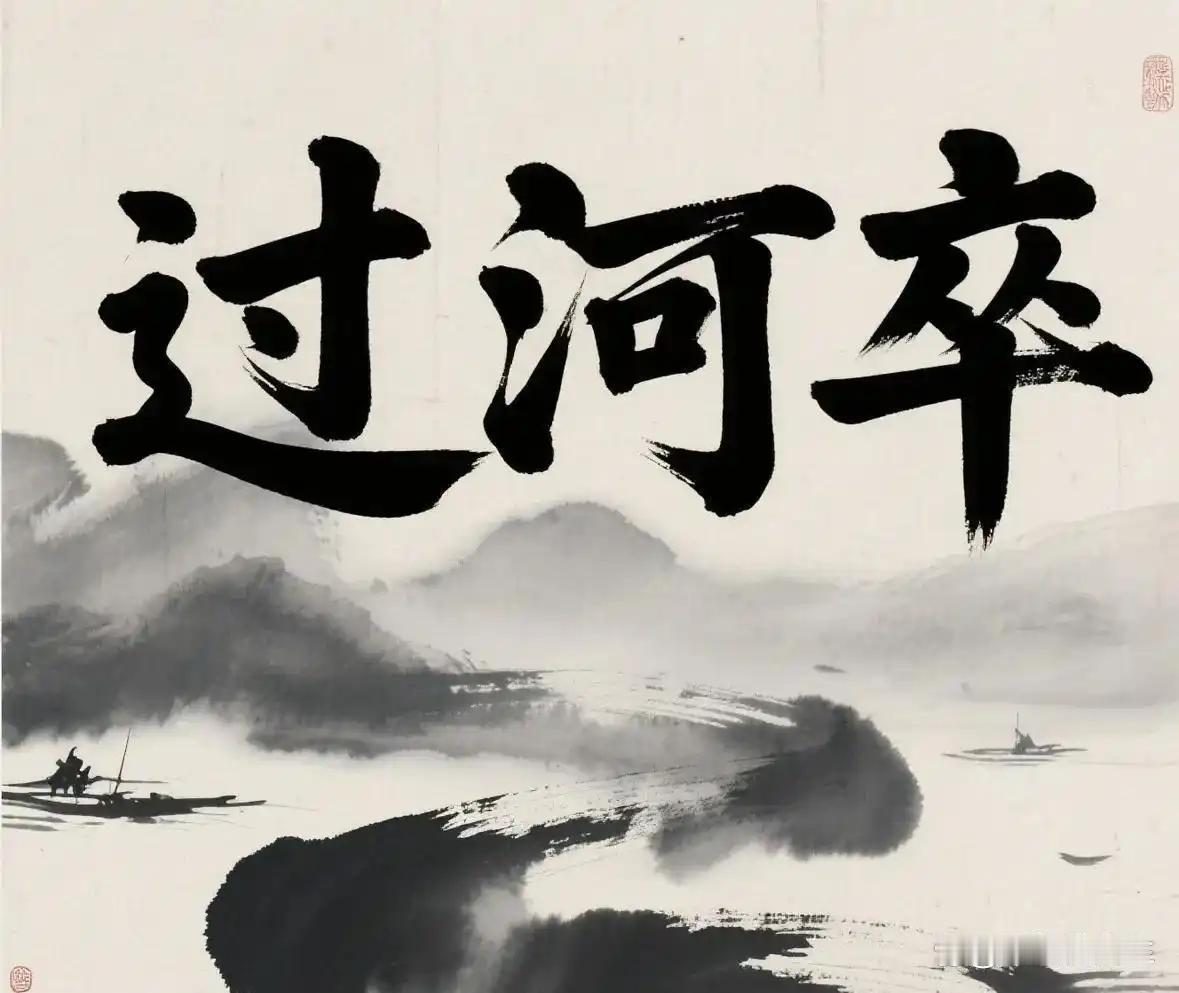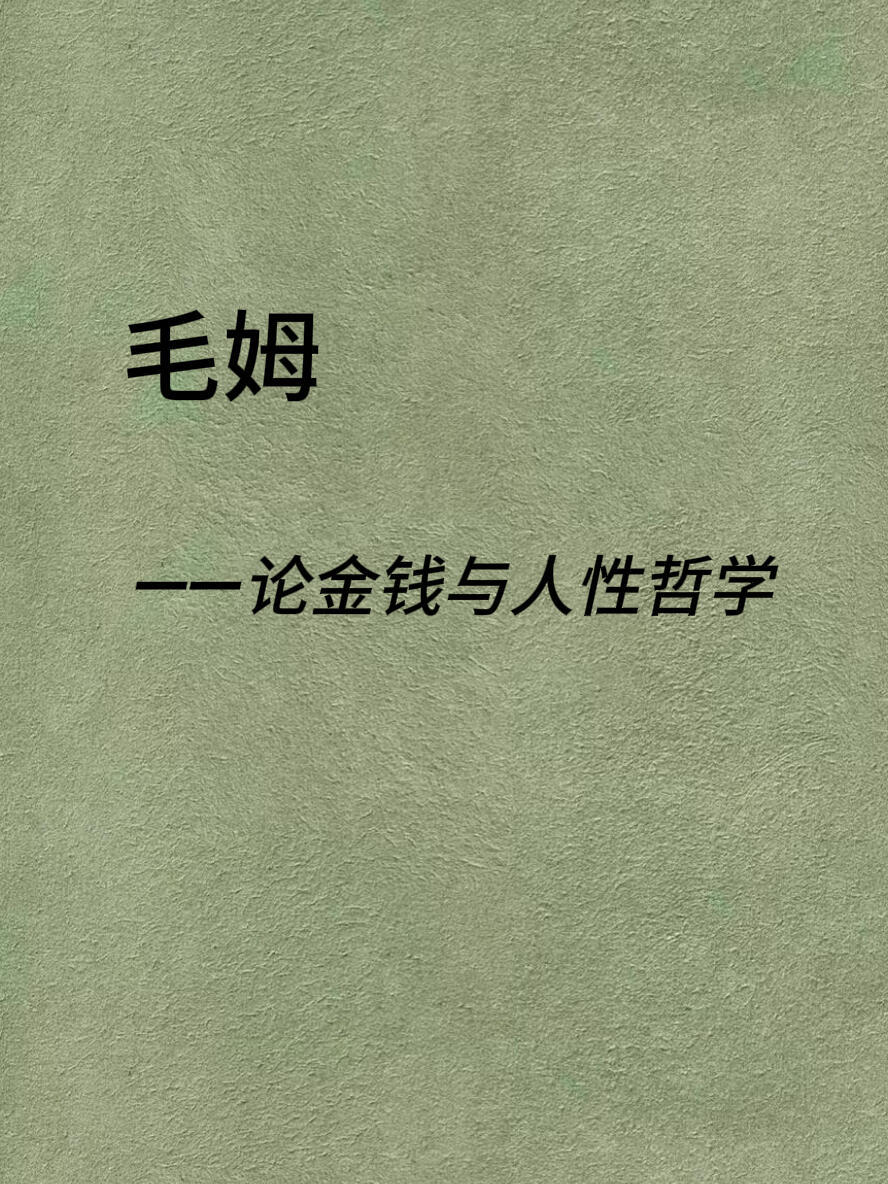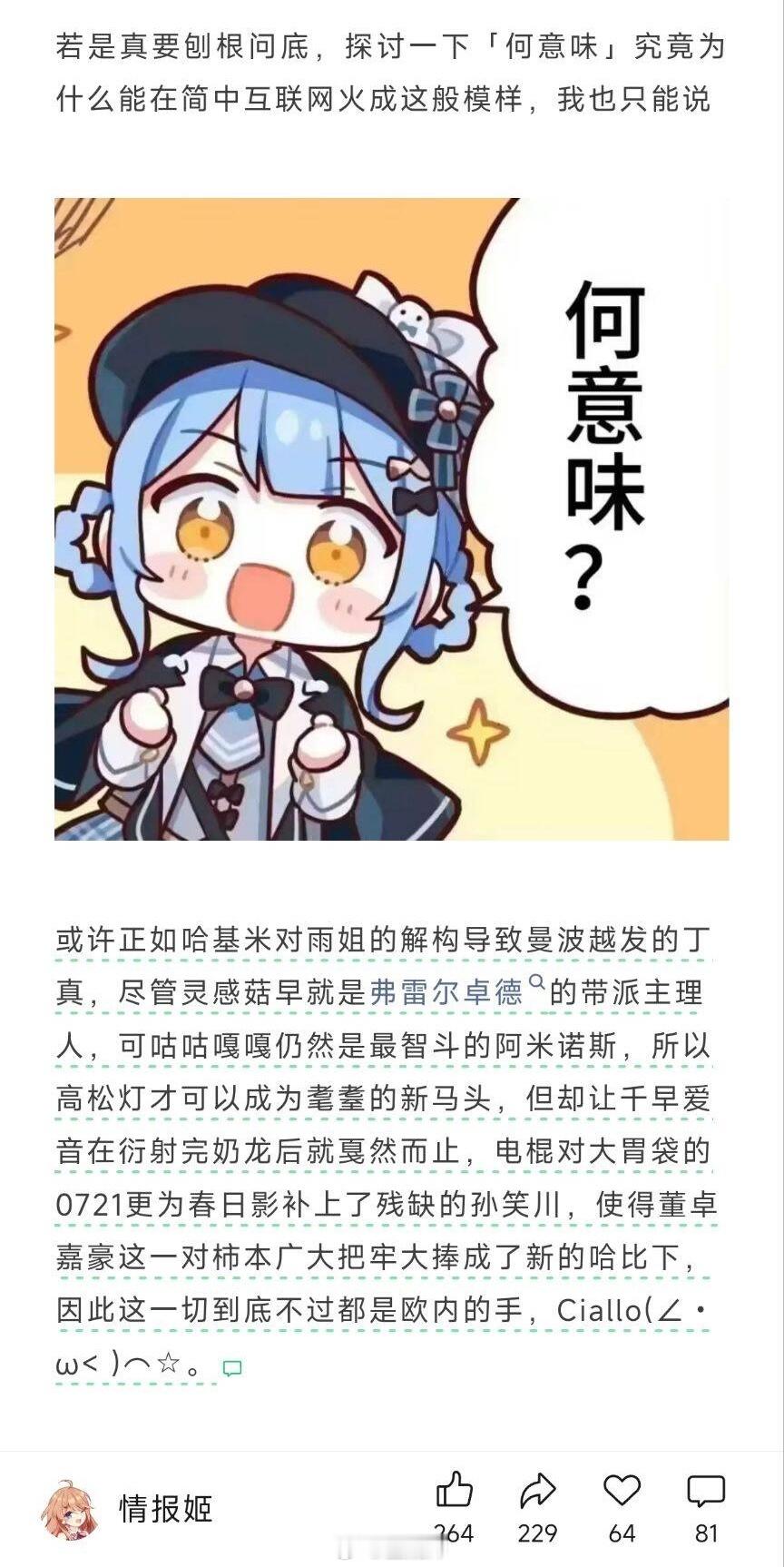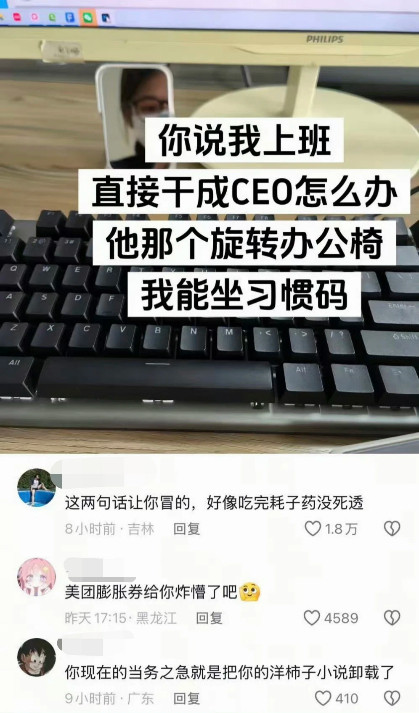【 序跋精粹 | 李传玺:回忆未必可靠 】
(文汇·笔会 2025-10-31 18:57 )
* 本文为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林徽因:大写的她》代序,作者:李传玺。
————————
《回忆未必可靠》 (李传玺)
标题是我这两年研究梁思成、林徽因所产生的感慨。
何以会有这个感慨?
读有关人民英雄纪念碑史料时,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谈到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人员时,竟然把林徽因写成了“凌徽因”。这本书还是当年参与者回忆性质的书,那时出版无论编辑还是作者都是很严谨的,出这个错,当我一看到,真是大大一愣。为什么会有此错呢?只能是一个原因:林徽因先生逝世较早,距此时已经有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又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冲击最频繁的艰难岁月,林先生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淡化。
“科学的春天”到来后,林徽因逐渐以中国现代文化人最闪亮的形象回归人们的视野。对她的回忆和纪念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又正是这种时间流逝以及由此带来的记忆的淡化,使得此类文章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此类失误。
再举一个例子。
1950年6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议题就是选定国徽图案。梁思成先生因为那几天太劳累病倒了,林徽因先生本来就病着。由于朱畅中先生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秘书,同时参与了国徽图案设计,梁先生就请他“做代表去会上听取意见”,朱畅中先生跟随张奚若先生前往参加。在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之时,他写了篇回忆文章,重点谈了国徽设计以及参加此次重要会议所见到的讨论国徽图案的情景:“会议室中间白墙上挂着两个国徽图案:左为清华方案,右为美院方案”,“参加会议的委员们,或坐或站,一边观看国徽图案,一边议论纷纷。他们各有所好,各有看法,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当时我站在旁边,心中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这捉摸不定的评选结果”,“大家正在纷纷议论之中,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周总理走到两个图案前细细观看一下后,就问大家意见如何。田汉先生首先对总理说,他认为中央美院的方案好,还说了些优点。有的委员也赞同田汉的意见”。(《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此书编辑委员会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26页)
别小看这么几句话,这可是重大历史事件,事关参会人员对国徽图案的态度与选择意见。看此次会议记录影印件,列席者就朱畅中一人。他的这回忆应该很重要,故而后来说到此次会议,朱先生的回忆都是关键参考资料,基本上都予以引用。
我初次看到这段,不仅准备引用,心中还产生联想:讨论国歌时,马叙伦先生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他的话首先得到梁先生的赞同,并提出词曲都保留。当时田汉先生就在场,他自己还谦虚说词有时间局限性。此番讨论国徽图案,没想到首先是田汉先生否定由梁思成、林徽因挂帅的清华图案,看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讨论国旗国歌国徽方案时,大家都是一本公心,没有存情面之私的。
但当我再对照影印记录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缺席人名字写着(我按原记录照抄):剪(作者按:应作“翦”)伯赞、钱三强、张澜、马寅初、梁思成、叶剑英、郭沫若、田汉、李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17页)梁思成先生没去,田汉先生也没去。没去的田汉何来此番不同意见?
还看一个例子。费慰梅作为梁思成林徽因最好的朋友,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一书,以纪念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在说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因抗战全面爆发离开北平时间时,她这样写道:“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曲莹璞、关超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9月第1版,第124页)可根据新版《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1935—1940)林徽因致费慰梅1937年9月19日信记载:“亲爱的人们: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不知从何说起。我们总还算是平安,一周前抵达天津,正乘船离开,准备前往青岛转济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7月第1版,第272页)此信一直由费慰梅保留着,明确地说明了梁林一家离开北平的时间是9月12日,和从天津继续逃亡的时间是9月19日。此信写得很短,一反她给费慰梅信总是长篇大论,正是由于乘船离开时间紧张。看来费慰梅在写作时是仅凭记忆来写的。她并没有去看看当时的信件。
由此我想说,即使是事件亲历者,时间一久,回忆未必可靠,在写作时必须注意与原始资料或档案相印证。
这本书里很多文章是对林徽因先生的“辨析”,在在证明回忆未必可靠。这两年印行的一些关于林徽因先生早期的史料(这些史料由于年代久远,也存在着一些时间编排上的错误),为这些辨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这些辨析不是对回忆者和纪念者所作出的贡献的贬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关心梁、林的读者“留下真实的注脚”(于葵语)。这些辨析更不是对林徽因先生包括梁思成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的否定,相反,会让他们的形象更清晰更鲜明更真实,让林徽因那大写的“人”更“风神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