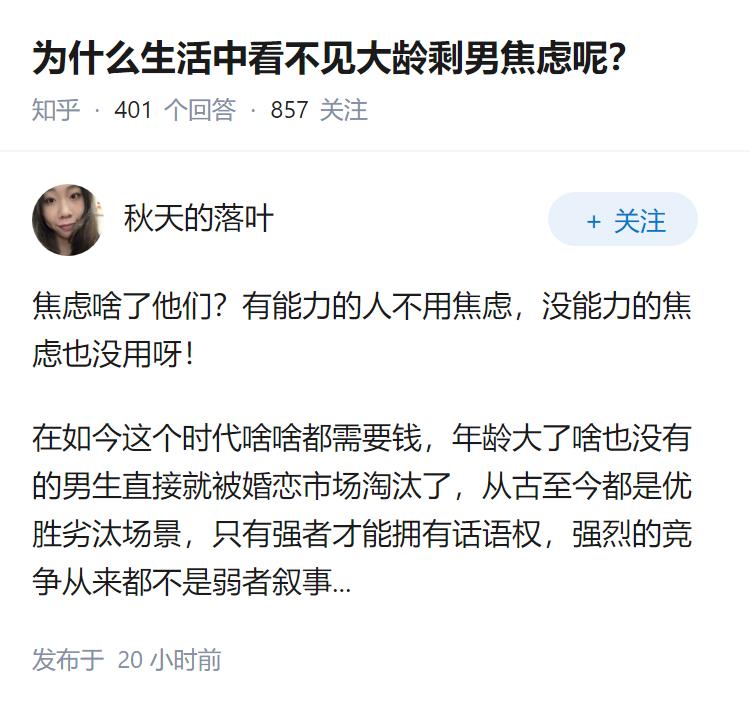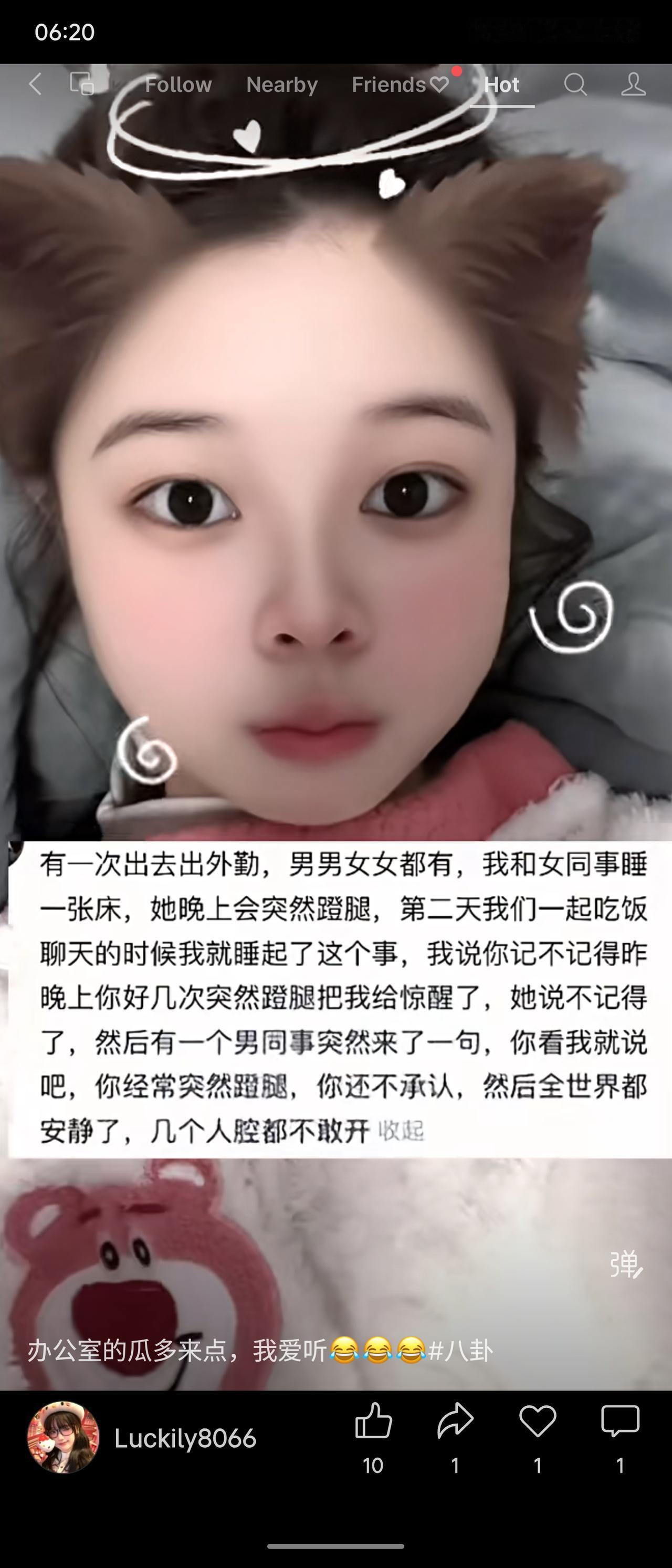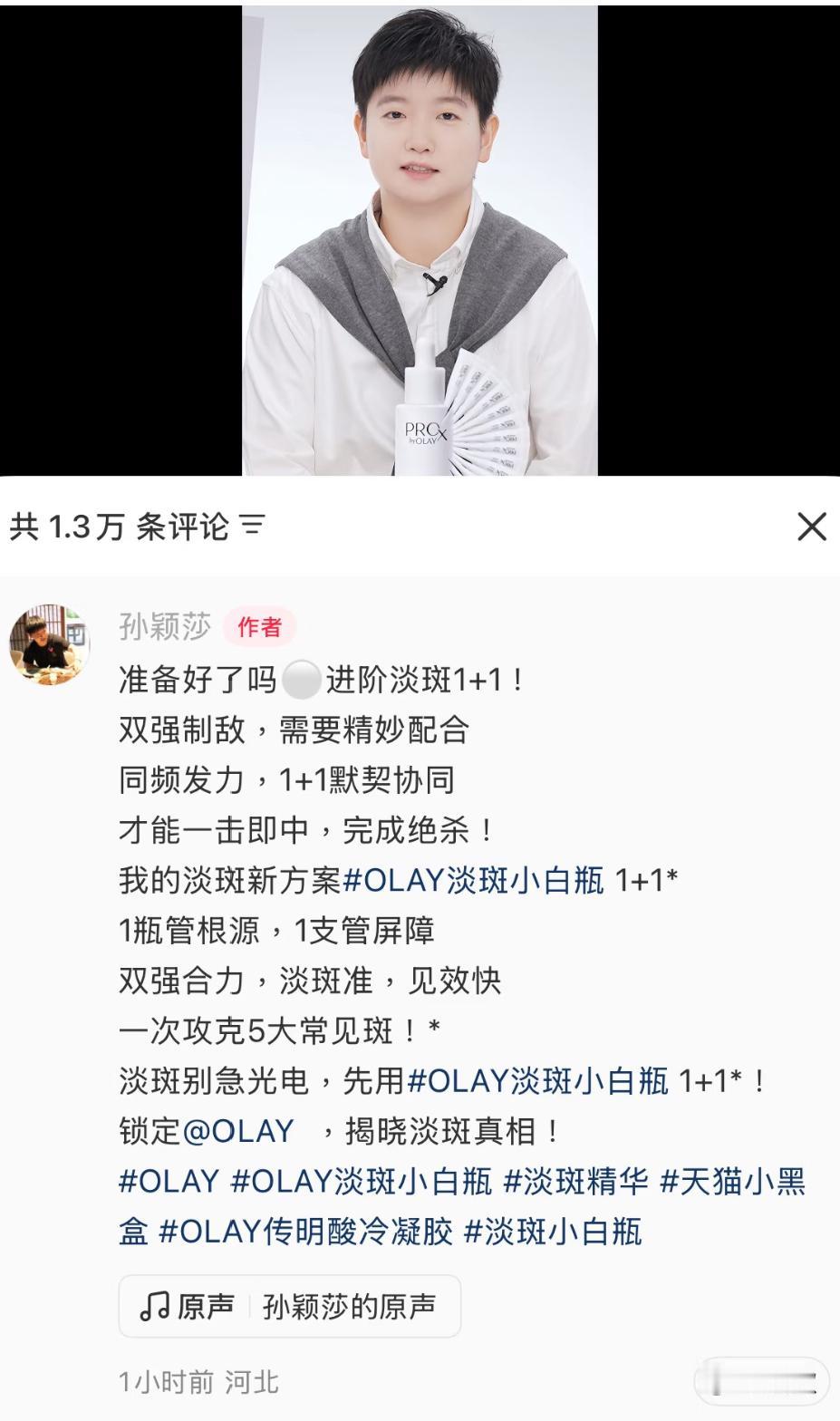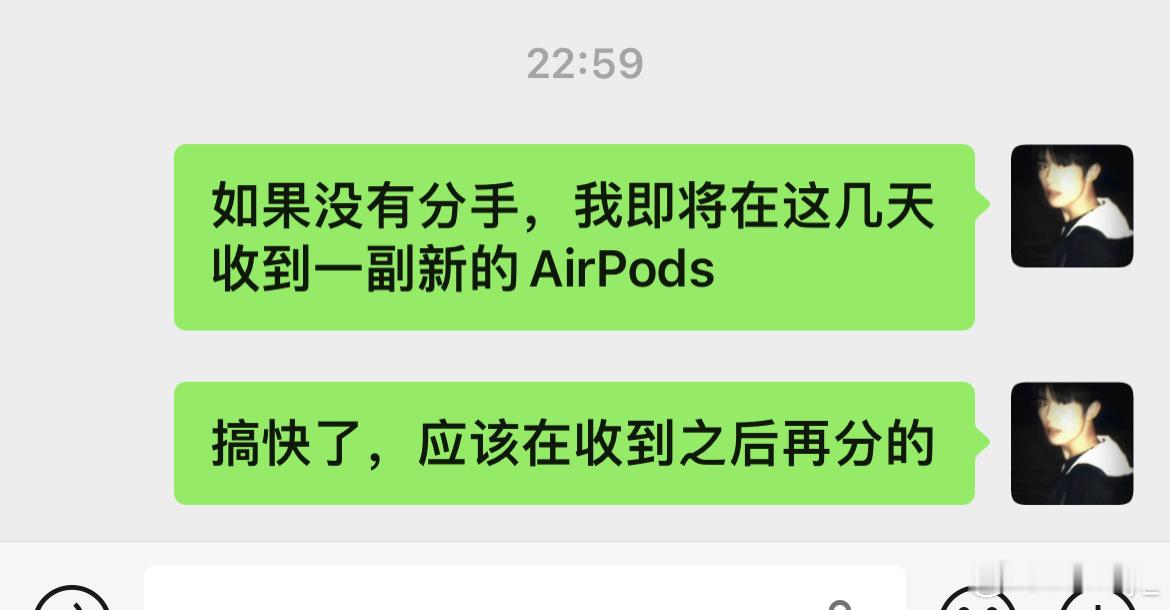正月初五,家族一年一度的聚餐,照例定在县城最气派的“聚福楼”。
大厅里摆了四张大圆桌,我们一家到得晚,只剩靠门那桌还有空位。爹妈局促地坐下,妈还特意把旧棉袄的袖口往里掖了掖。
菜刚上齐,主桌那边就传来大伯母王秀英拔高的嗓门:“哎哟,这不是建国家吗?今年来得可真‘准时’,专挑开饭的点!”
满桌亲戚哄笑。我爸周建国,我妈李桂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我爸闷头“嗯”了一声,拿起桌上的廉价香烟,手有点抖。我妈则垂下眼,盯着面前那盘凉拌黄瓜,筷子都没动。
我心里一股火“噌”地窜上来。大伯周建业早年承包工程发了家,大伯母王秀英就自觉成了家族的“太后”,年年聚会都要找点由头踩我们家一脚,显摆她家的优越。
“妈,吃菜。”我夹了块排骨给我妈。
“吃啥呀!”王秀英的声音又飘过来,她端着酒杯,扭着腰走到我们这桌,居高临下,“桂芳啊,不是我说你,你家周岩结婚也三年了吧?当初彩礼才给了八万八,婚房还是二手房。你看我儿媳妇,彩礼二十八万八,婚房一百四十平,市中心!这养儿子啊,就得有本事,没本事就别硬撑,穷酸气传给孩子,丢人!”
“你……”我猛地站起来,拳头攥紧。
“周岩!”我爸低喝一声,用力拉我坐下。他额角青筋突突地跳,却还是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大嫂,喝酒,喝酒。”
王秀英得意地抿了一口酒,却没走,目光扫过我妈身上那件穿了五六年的暗红色毛衣:“桂芳,你这毛衣起球起得厉害,我家保姆都不穿了。改天我收拾几件我不要的,给你拿去,好歹过年穿个新鲜。”
我妈肩膀微微发抖,头埋得更低,一滴眼泪悄无声息砸进面前的碗里。
耻辱感像冰水浇透我全身。我看着爹忍气吞声的侧脸,看着妈无声的眼泪,血液往头顶冲,可脚像钉在地上。顶撞长辈,尤其在这么多亲戚面前,后果是什么?爸妈以后在家族里更没法抬头?
就在我浑身僵硬,气得牙齿咯咯响时,桌下,一只温暖的手轻轻覆上我的膝盖。
是我老婆,林薇。
我转过头。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甚至嘴角还带着一点惯常的温和弧度,但那双看着我眼睛,亮得惊人,里面没有委屈,没有害怕,只有一种沉静的、跃跃欲试的火苗。
她凑近我,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气音,一字一句,清晰地问:
“老公,我能撒个泼吗?”
我愣住了。看着她清澈坚定的眼神,脑海里闪过我们结婚这三年来,她受的委屈。因为我家的“穷”,明里暗里被亲戚们比较、调侃。她从不抱怨,总是笑笑说“日子是自己过的”。但我知道,她心里都记着。
此刻,她问我,不是问她能不能忍,而是问她能不能战。
为我爹娘而战。
所有的犹豫、顾虑,在看到她眼神的瞬间被击得粉碎。去他的长辈面子,去他的家族规矩!我爹娘都快被欺负到泥里了!
我反手用力握住她的手,看着她,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赶紧的!”
林薇笑了。那笑容不再是平时的温和,而是带着一种豁出去的、明亮又锋利的光彩。
她轻轻抽回手,优雅地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然后,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
“大伯母。”她的声音不高,却奇异地压过了大厅的嘈杂。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王秀英斜着眼,一副“看你还能翻出什么花”的表情。
林薇没理她,径直走到大厅角落那个平时用来唱卡拉OK的小台子上,拿起了话筒。
“喂,喂。”她试了试音,声音通过音响传遍整个大厅,“各位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过年好。趁着今天人齐,菜也上齐了,我,周岩的媳妇林薇,有点话,想跟大家唠唠,也请大伯母一起听听。”
王秀英脸色一变:“你干什么?大过年的,耍什么猴戏!”
“大伯母别急,就是唠唠家常。”林薇笑得特别和气,却拿着话筒,一步不让,“刚才大伯母心疼我妈,说要送她几件旧衣服,这份‘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呢,我也正好有点事,想跟大伯母,还有在座的各位,算算清楚。”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所有人都放下了筷子,好奇地看着这个平时温声细语的新媳妇,不知道她要唱哪出。
“第一笔账,”林薇开口,声音清晰平稳,“三年前,周岩跟我结婚。彩礼八万八,婚房是二手房,六十平。大伯母刚才说,这‘穷酸’,‘丢人’。行,那我们看看,这八万八彩礼,这二手房,是怎么来的。”
她拿出手机,连接上大厅的投影仪——这设备平时没人用,今天倒是派上了用场。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张照片和表格。
“这是我公公,周建国,过去二十年,在建筑工地的记工本照片,有些字都模糊了。一年三百天,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这是他近五年的银行流水,每月进账从来没超过六千,出账大部分是给我婆婆买药,以及……资助周岩上大学。”
屏幕上滚动着详细的数字。大厅里鸦雀无声。
“这是我婆婆,李桂芳,在环卫站工作十五年的记录。凌晨四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风雨无阻。她的工资流水,每月三千二。她的体检报告,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
我妈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是夏天她穿着橙色工服,在烈日下扫街的背影,汗湿透了衣服。
我爹妈怔怔地看着屏幕,我妈的眼泪流得更凶,但这次,是另一种情绪。
“八万八彩礼,是他们从牙缝里省了五年,加上卖掉家里唯一一头过年猪才凑齐的。六十平的二手房,首付二十万,是他们掏空了所有积蓄,又找信得过的老兄弟借了五万才够的。”林薇的声音有些发颤,但依旧用力撑着,“他们没本事?是,他们没本事赚大钱,没本事给你们送礼攀关系,但他们用一辈子的力气,干干净净、挺直脊梁地把儿子养大,供他读书,帮他成家!这丢谁的人了?丢你们这些穿金戴银、看着他们吃苦还踩上一脚的人的脸了吗?!”
最后一句,她几乎是喝问出来的,目光如刀,直刺王秀英。
王秀英脸涨成猪肝色,张着嘴想反驳,却被林薇的气势和眼前铁一般的事实堵得说不出话。
“第二笔账,”林薇深吸一口气,操作手机,切换画面,“大伯母,您儿子,我堂哥周伟,三年前结婚,彩礼二十八万八,婚房一百四十平。好,风光!那我们来看看,这风光的底子。”
屏幕上出现几张模糊的聊天记录截图和转账记录。
“这是三年前,大伯,周建业,私下找我公公借钱的记录。金额八万,理由是‘资金周转’。至今未还。这是借条照片。”林薇放大图片,上面有我爹歪歪扭扭的签名和红手印。
“这是去年,堂哥周伟想换车,首付不够,大伯母您亲自打电话给我婆婆,‘借’两万块钱‘应应急’的记录。我婆婆当时住院等着交钱,都没舍得用,取出来给了您。也没还。”
大厅里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几个长辈的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王秀英尖叫:“你胡说八道!伪造记录!周岩,你管不管你媳妇!”
我站起来,走到林薇身边,和她并肩站着,拿过她手里的话筒:“大伯母,这些记录,银行、微信都有底,是不是伪造,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打印流水,报警查证。您敢吗?”
王秀英被我噎得后退一步。
林薇接过话筒,继续放出第三颗炸弹:“第三笔账,也是最让我恶心的一笔账。大伯母,您身上这件貂皮大衣,新款,至少三万块吧?您手上这金镯子,粗的,也得两万?您孙子,我小侄子,脖子上那块金锁,怕是也不便宜。”
她话锋一转,语气冰冷:“可您知不知道,去年秋天,我婆婆关节炎发作疼得走不了路,想去市里医院看看,打电话问您,能不能借三千块钱周转一下,您是怎么说的?”
林薇点开一段录音。
王秀英尖利刻薄的声音从音响里炸开:“三千块?李桂芳,你儿子媳妇是死了吗?找我要钱?我哪有闲钱!自己命贱身子娇贵,疼死算了!”
录音播放完,整个“聚福楼”大厅死一般寂静。所有亲戚,包括之前附和王秀英的那些,都露出了难以置信和尴尬的神情。
我妈再也忍不住,捂住脸,失声痛哭。我爸老泪纵横,紧紧搂住她的肩膀。
王秀英彻底慌了,指着林薇:“你……你偷录!你心机深!周建业,你看看!这就是你侄媳妇!”
一直阴沉着脸坐在主桌的大伯周建业,猛地一拍桌子,却不是冲着我们,而是冲着王秀英怒吼:“闭嘴!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
林薇关掉投影,放下话筒,拉着我走下小台子。她没有再看瘫软在椅子上的王秀英一眼,而是走到我爹妈面前,蹲下身,握住我妈粗糙的手。
“爸,妈,以前是儿子没用,让你们受委屈了。”我声音哽咽,也跟着蹲下,“从今往后,谁再敢欺负你们,我和小薇,第一个不答应!咱们家是穷,但穷得不偷不抢,不欠谁不亏谁,脊梁骨是直的!用不着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日子!”
我妈紧紧抱住林薇,哭得说不出话。我爸用力拍着我的背,一遍遍说:“好,好儿子,好媳妇……”
那天之后,我们一家提前离开了聚餐。听说后来,大伯周建业当众狠狠训斥了王秀英,并郑重向我们家道了歉,承诺一周内归还所有借款。
家族群里的风向也变了。之前沉默的亲戚,开始私下给我们发信息,说“小薇真厉害”、“早就看不惯了”、“以后有啥事吱声”。
更重要的是,我爹妈变了。腰杆挺直了,笑容多了,我妈甚至敢在家族微信群里发她跳广场舞的视频了。
回家的车上,我紧紧握着林薇的手。
“老婆,今天……谢谢你。你那不叫撒泼,叫有理有据的维权,叫帅炸了!”
林薇靠在我肩上,笑了:“其实我也怕。但看到爸妈那样,我就忍不住了。老公,谢谢你当时说‘赶紧’。”
“谢什么,”我亲了亲她的额头,“你为我爹娘开战,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以后,咱们家,互相守护,谁也别想欺负!”
家庭不是攀比炫耀的擂台,而是遮风避雨的港湾。真正的体面,不是锦衣玉食踩低别人,而是无论贫富,都能维护家人的尊严,珍惜彼此的情分。当底线被触碰,温柔不是懦弱,勇敢站出来,用智慧与事实守护所爱,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