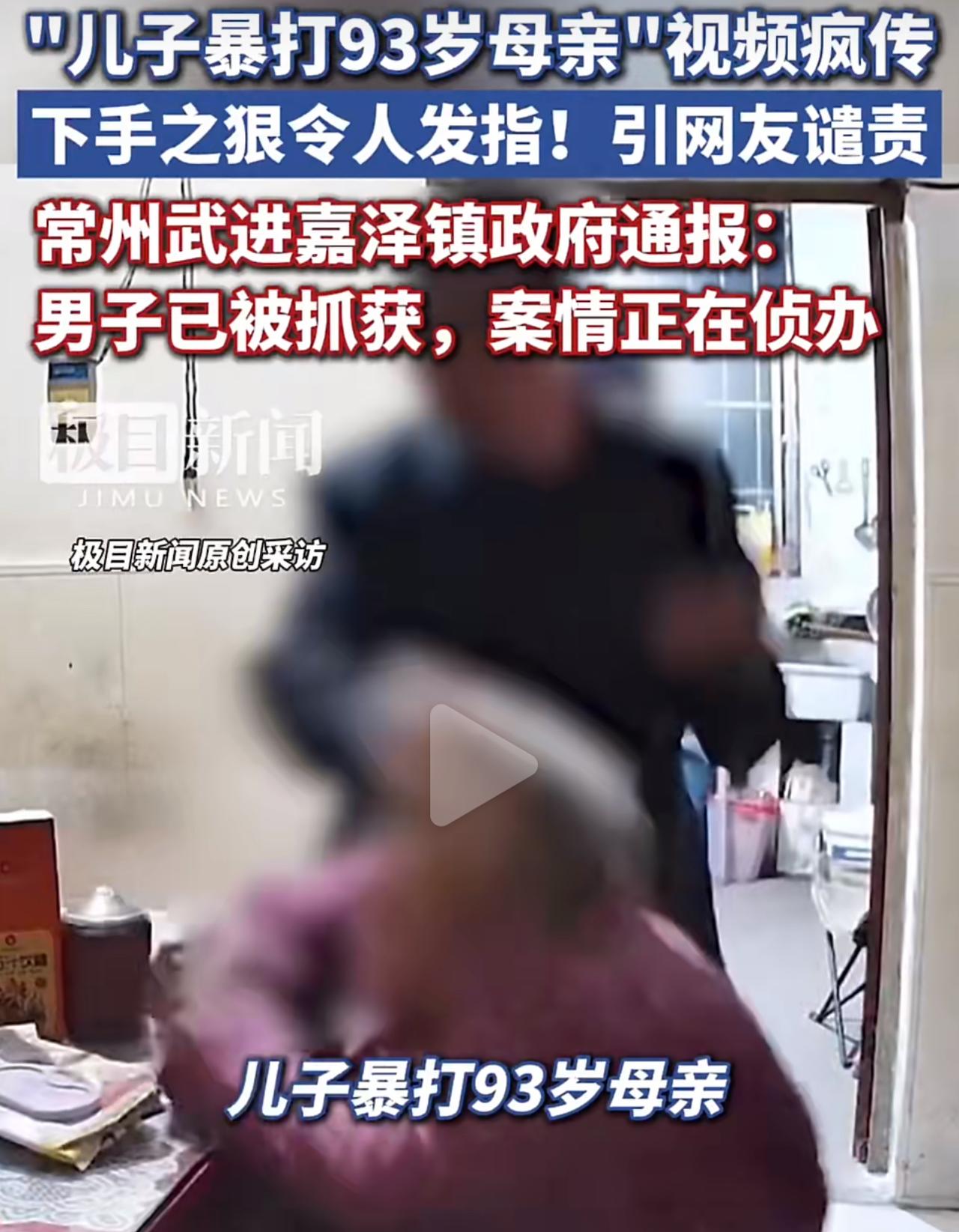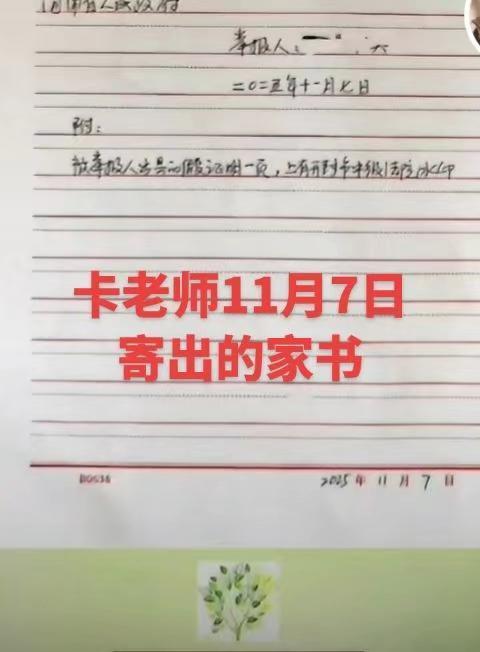1984年的江南初冬,寒意已浸透了常州武进的田野。湖塘镇田舍村的这片土地上,推土机的轰鸣打破了村庄延续百年的宁静 —— 武进供销干部培训学校的基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寻常的施工,即将揭开一段被黄土掩埋了十四个世纪的隋唐往事。

11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推土机司机老王像往常一样操控着机械平整土地。当铲斗挖到两米多深时,突然传来 “咔嚓” 一声闷响,紧接着是砖块碎裂的清脆声响。经验丰富的老王立刻停了机器,跳下车扒开浮土查看,只见一层排列整齐的青砖在泥土中若隐若现,砖缝间还粘着潮湿的红泥。“这底下怕是有老东西!” 老王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让人联系了工地负责人。
消息很快传到了武进县博物馆。时任馆长的周裕兴正整理着一批六朝文物,接到电话后立刻带上工具赶往现场。“当时心里又激动又忐忑,常州地区隋唐墓葬发现得少,尤其是保存完整的砖室墓更是罕见。” 多年后周裕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难掩兴奋。抵达现场后,考古队员们用洛阳铲进行试探,发现地下存在大面积砖构遗迹,且范围远超预期。常州市博物馆随即介入,两支队伍迅速组成联合考古队,一场跨越数月的发掘工作就此展开。

最初的发掘并不顺利。初冬的阴雨让工地泥泞不堪,考古队员们穿着胶鞋在泥地里作业,一脚踏下去就是半尺深的烂泥。经过十余天的清理,一个两米高的封土堆逐渐显露出来,封土之下,两座南北并列的砖室墓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两座墓间距只有0.5米,共用一个土坑,这种‘同茔异穴’的布局在隋代墓葬中十分典型。” 考古队领队指着墓葬布局解释道。随着封土被彻底清除,墓葬的形制愈发清晰:两座墓葬均朝西向,大小几乎一致,南侧墓葬长5.1米、宽2 米、残高1.88米,北侧墓葬则略高一些,达2.1米,仿佛一对并肩矗立的千年卫士。
清理墓门的过程充满了悬念。墓门采用双重券结构,外层封门墙由青砖交错叠砌而成,异常坚固。考古队员们用小锤和钢钎小心翼翼地拆解,生怕损坏内部结构。当封门墙被打开一个缺口时,一股夹杂着泥土气息的古老气味扑面而来。借着灯光向内望去,墓室两侧壁向外弧凸,形成独特的腰鼓形,后壁底部微微外凸,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营造工艺。
进入墓室后,更令人惊叹的细节逐一呈现。墓室地面铺着单层横砖,排列得严丝合缝,中后部隆起的棺床略高于地面,边缘用竖砖锁口,下方还垫着一排侧立砖,这种设计既能固定棺木,又能起到防潮作用。“你看这些砖的排列,看似随意实则暗藏玄机。” 考古队员蹲下身,指着棺床边的砖垛介绍,“南侧墓的左右壁和后壁各有一个砖垛,北侧墓的左右壁也有,这些都是用来固定木棺的,防止棺木在地下移位。”
墓室的墙壁堪称隋代建筑艺术的缩影。左右两壁各有两组假直棂窗,后壁还有一组,每组直棂窗中部是一个或三个长方形大窗,两侧排列着两至三个条形窗格,窗格之间的砖缝细密均匀,仿佛真窗一般。更令人称奇的是,每组直棂窗上方都砌有长方形灯龛,“这些灯龛当年应该摆放着油灯,既能照明墓室,也寄托了墓主人对光明的向往。” 考古队的年轻队员抚摸着灯龛边缘,想象着千年前的下葬场景。

墓顶的营造工艺同样令人赞叹。墓室后壁从0.5米高处开始起券,两侧壁则从1 米高处起券,最终在顶部攒尖,形成一个规整的穹窿结构。“这种起券方式既稳固又美观,是六朝墓葬工艺的延续和发展。” 周裕兴馆长解释道,“隋代统治时间短,墓葬形制大多承袭前朝,这座墓的腰鼓形墓室、假直棂窗等特征,都能在六朝墓葬中找到渊源。”
发掘过程中,最让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墓砖上的文字。在两座墓室内侧的部分壁砖上,发现了阴线刻划的文字,字迹流畅随意,多为数字和简单符号。“这些应该是工匠制砖时随手刻下的,可能是计数标记,也可能是工匠的代号。” 文字专家仔细辨认后推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刻字,为研究隋代制砖工艺和工匠制度提供了珍贵线索。墓砖的种类也十分丰富,有长方形、楔形等多种形制,楔形砖又分为平面梯形和侧面梯形,大小规格近十种,混杂使用却不显杂乱,展现了隋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技艺。
随着发掘深入,陪葬品陆续出土。南侧墓葬出土了10件文物,包括2件青瓷盘口壶、1件青瓷碗、6件青瓷灯碗和 1 枚鸟兽规矩纹铜镜;北侧墓葬同样出土10 件文物,有1件青瓷盘口壶、1件青瓷双唇罐、7件青瓷灯碗和1件饼形瓷坯。这些文物虽不算奢华,却工艺精湛,尤其是青瓷制品,釉色莹润,造型规整,尽显隋代青瓷的烧制水平。“你看这件青瓷盘口壶,盘口硕大,颈部修长,腹部丰满,是隋代青瓷的典型器型。” 文物修复师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出土的瓷器,“北侧墓的青瓷双唇罐带有初唐风格,这为判断墓葬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棺木早已在千年岁月中腐烂殆尽,只留下少量漆皮和残棺钉,但考古队员们通过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逐渐勾勒出墓主人的身份轮廓。“两座墓葬规模中等,随葬品以生活用具为主,没有金银玉器等贵重物品,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当地的富裕平民或低级官吏。” 周裕兴馆长分析道,“南侧墓的形制和文物更具隋代早期特征,北侧墓则带有初唐风格,结合历史背景推测,南侧墓为隋代墓,北侧墓可能建于隋末唐初,墓主人或许是一对夫妻,先后下葬于此。”

这次发掘共清理出六座砖室墓,除了这两座隋代墓葬外,其余四座均遭严重破坏,文物所剩无几。而这两座隋代墓葬之所以能保存相对完好,得益于其深埋地下的地理位置和坚固的砖室结构。“隋代统治只有三十八年,存世的墓葬数量不多,像这样保存完整、形制清晰的更是凤毛麟角。” 联合考古队在发掘报告中写道,“田舍村隋墓的发现,为研究隋末唐初的墓葬制度、丧葬习俗以及江南地区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队员们在清理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座墓葬的形制虽基本沿袭六朝,但在细节上已有创新,比如假直棂窗的设计更加精巧,灯龛与窗格的组合更具装饰性,这些变化印证了隋唐之际丧葬文化的演变。“常州地处江南,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这座墓葬既保留了南方六朝墓葬的传统,又吸收了北方墓葬的某些元素,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 考古专家这样评价。
随着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文物整理和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出土的青瓷制品被送往实验室进行脱水处理,墓砖上的文字被逐一拓印记录,墓葬的测绘数据也被详细归档。如今,田舍村隋墓已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静静地躺在供销干部培训学校的校园内,成为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坐标。

站在墓址之上,仿佛能听见千年之前的营造声。那些精心烧制的墓砖,那些巧夺天工的窗格,那些承载着生活气息的瓷器,都在诉说着隋代江南的社会风貌。田舍村隋墓的发现,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隋唐时期的历史之门,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短暂而辉煌的时代,感受江南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
“考古的意义,就是让沉睡的历史苏醒。” 周裕兴馆长望着保护完好的墓址,感慨地说,“这两座墓葬不仅是常州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见证了朝代更迭,承载着文化传承,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朱由检对不起很多人,但是对洪承畴是真的极好的[6]](http://image.uczzd.cn/2131519740669763080.jpg?id=0)

![确实,比香火上周仓都欺负人[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340569423863820340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