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 李克农
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枪声回荡在1950年的天空,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意地向蒋介石呈上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千八百多个名字。“委座,共匪在台的地下组织,已被我们一网打尽。” 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北京的“特工之王”李克农,早在二十年前,就悄悄埋下了一颗谁也不知道的 “活棋” 。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台北马场町,几声枪响划破天际,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英雄倒在了血泊中。此时,距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才刚刚过去三个月。
这个曾经走过长征的台湾籍老党员,在被捕后没几天就顶不住了,一口气供出了包括吴石将军在内的超过一千八百人。国民党特务按照他给的名单疯狂抓人,最终有一千一百多位同志英勇就义。
一时间,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网络被彻底摧毁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在台北郊区一个不起眼的杂货铺里,另一支神秘的“幽灵小组”,正屏住呼吸,悄然运转着……

图 |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
从书记到叛徒的蔡孝乾1950年初的台湾,整个岛屿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街小巷,特务像猎狗一样四处搜寻;电线杆上、茶馆门口,通缉令贴了一层又一层。
这场风暴的源头,都源于一个人——当年1月29日被捕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这个原本应该宁死不屈的“最高领导”,被抓进去才三天就彻底垮掉了。
蔡孝乾是台湾彰化人,还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1946年,组织上派他组建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担任书记,这本来是对他极大的信任。
可谁想到,到了台湾后,他完全变了个人:贪污组织的活动经费,甚至跟16岁的小姨子同居。更离谱的是,他居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写着“吴次长”,连朱枫的联系方式都直接记在钞票上,这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火。

图 | 蔡孝乾
第一次被抓后,蔡孝乾骗特务说自己只是个普通联络员,趁着看守不注意逃了出去。躲了两个月后,他实在受不了清苦的躲藏生活,竟然冒险跑到嘉义一家高档西餐厅去吃牛排解馋,结果被眼尖的特务认出来,再次落网。
这一次,他彻底投降了,不但要求让他的小姨子马雯娟跟他一起关在监狱里作为交代条件,而且在一周之内就把知道的所有情报和人员名单全都供了出来。
他这一开口,整个台湾的地下党组织瞬间土崩瓦解。特务按照他提供的名单抓了1800多人,其中1100多人被杀害。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首当其冲,成为了这场叛变中最大的牺牲品。
深谋远虑:李克农的两手准备当蔡孝乾叛变的紧急消息传到北京,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可有一个却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点了支烟——他就是被称为“特工之王”的李克农。
他不是不心痛,而是心里有底。这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早在1931年就已经悄悄地布下了一颗“活子”。这颗棋子,就连蔡孝乾都毫不知情。
李克农为了应对这种最坏的情况,早就定下了 “单线联系,严禁横向接触” 的铁律。这意味着每个情报人员只认识自己的上线,小组里的其他人叫什么、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一概不知。

图 | 李克农和夫人
当时不少同志私下里抱怨:“这规矩也太死板了吧?传个情报要绕好几个弯,效率太低了。”可谁能想到,正是这份看似“低效”的规定,在蔡孝乾叛变后成了许多同志的救命符。
李克农的布局是双线并行的:吴石将军走的是“军事策反线”,专门负责争取国民党高层军官;而他直接领导的中社部潜伏小组,则负责摸清台湾的基层布防、兵力调动、碉堡位置这些具体的“硬核情报”。
两条线平时各干各的,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这种看似“资源浪费”的安排,在危机爆发时却成了神来之笔——吴石那条线出了事,这边却安然无恙。
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在吴石等人牺牲后,李克农留下的这张底牌开始悄悄地发挥作用。这些无名英雄们,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智慧。
于非和萧明华领导的“心理学讲座室”小组位于台北厦门街113号。萧明华表面上是台湾师范学院的老师,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开办心理学讲座。
她从参加讲座的六十多名学员中,慢慢挑选出25名进步青年,把他们发展成为情报力量。这个年轻的浙江姑娘,把课堂当成联络点,用课本传递暗号,谁也没想到这位文静温和的女教师竟然是地下工作者。
他们之间有个生死约定:如果窗外竹竿上没有晾晒衣物,就是危险信号。1950年2月,特务突然闯进门来,萧明华冷静地取下竹竿上的旗袍,面对审讯半个字都没有透露。
在监狱里的278天里,她受尽了各种酷刑,四肢都被打断了,却始终坚贞不屈。她甚至用“七颗鱼肝油”的方式传递信息——“七”在他们的暗号里就是“去”的意思,警告战友赶快撤离。1950年11月8日,她英勇就义,年仅28岁。

图 | 萧明华
苏艺林则是潜伏在国防部三厅的中校机要参谋,能接触到最核心的军事部署。吴石牺牲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海南岛防卫方案》拍成微缩胶卷送了出去。
情报传递的路线极其复杂:先托联络员送到香港中转,再从香港转到广州,最后送到上海,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12天。这份标注着防御工事和兵力部署的情报,后来被韩先楚将军的40军在横渡琼州海峡时使用,为解放海南岛立下了大功。
程一鸣则是另一颗深藏的棋子。他于1926年入党,1931年就受命打入中统内部。为了完成任务,他必须彻底“黑化”——说反共的话要铿锵有力,办反共的差要雷厉风行。
1949年他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进入保安司令部担任少校参谋,负责内部审查,成了专门揪“共谍”的人。这个特殊的岗位让他能够借“审查”之名,行保护同志之实。
当蔡孝乾供出的名单送到他桌上时,他震惊地发现自己亲手发展的两名联络员赫然在列。他连夜“提审”这两人,以“证据不足”为由将他们释放,并安排货车把他们送到乡下隐蔽起来。

图 | 程一鸣
生死较量:危机中的情报工作在台湾地下组织遭遇毁灭性打击的极端环境中,这些留守的情报人员每一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的情报传递方式极其隐秘。程一鸣用米汤当墨水,把情报写在家书的字里行间,晾干后毫无痕迹,收信人用碘酒一擦才能显影。这些信件通过一位做茶叶生意的朋友带出台湾,辗转送到香港,再转回大陆。
有一次,程一鸣的信在海关被拦了下来,工作人员要拆开检查。他立刻进入角色,一把抢过信件,眼眶发红,声音颤抖地说:“这是我妈等了半年的家书!她病在床上就盼着这封信,你们凭什么拆?” 他吵得理直气壮,演得情真意切,对方反而心虚了,最后摆摆手放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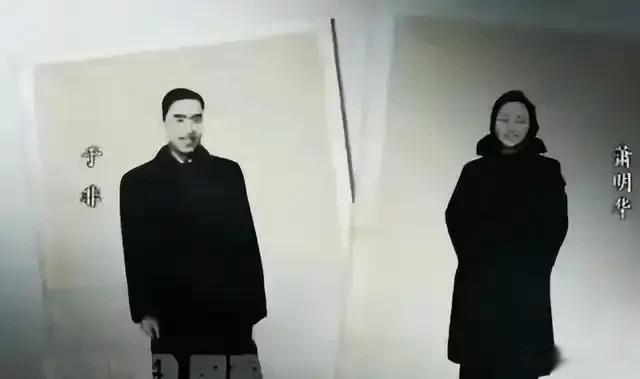
走出海关,他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湿透了。
与此同时,于非和苏艺林则在3月的一个深夜,趁苏艺林同事家中突发状况,将钥匙骗到手,携带微型相机潜入国防部档案室,拍下台湾全岛的军事部署、潮汐、暗堡等核心机要图纸。
这些胶片被封进防水袋,由于非伪装成商人,经香港中转送回上海。这些宝贵的情报后来直接用于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作战部署。
为了不暴露身份,这些潜伏者必须活得像个“真特务”。程一鸣开会时得高喊“肃清共匪”,酒桌上还得跟保密局的人称兄道弟,吹牛扯皮。
但散会后,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墙上的台湾地图发呆——那上面的每一个地名,都连着他救不了的同志,一个他不能相认的战友。
英雄终归与叛徒结局这些潜伏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最终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1964年,程一鸣终于等到机会,借着去澳门出差的名义,带着《金门防御部署图》、《国民党潜伏特务名单》和五支无声手枪,悄然回到了祖国怀抱。
消息传回台北,蒋经国气得当场摔了电话,连夜下令清洗整个情报系统。台湾对大陆的情报网,好几年都没缓过劲来。

图 | 蒋介石和蒋经国
于非在战友相继牺牲后,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潜伏,后来还发展了新的联络人,硬是把这条情报线保住了。直到局势缓和,他才绕道返回大陆,带回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而谢汉光则是另一名幸存者。蔡孝乾叛变那天,同事递来张伯哲的亲笔信让他快跑,他刚翻过后墙,特务就踹开了办公室的门。
靠着农民杨溪伯的掩护,他在深山里顶替了失踪村民叶依奎的身份,种杉树、采草药,一躲就是38年。晚上摸着新婚妻子的照片偷偷流泪,白天对过去的事半个字都不提,直到1988年才重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萧明华的遗骨直到1982年才被送回大陆,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于非亲笔在她的墓碑上写下三个字:“归来兮”——那不只是诗意的表达,更是一个沉甸甸的誓言的兑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叛徒蔡孝乾投敌后加入国民党,被授予少将军衔,长期在国民党保密局的监控下从事“匪情研究”。他住着特务专门给他盖的房子,死后还有完整的葬礼,1982年在台湾病逝。
而萧明华牺牲时只有28岁,苏艺林就义时36岁,吴石在临刑前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绝笔诗。
李克农的底牌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忠诚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