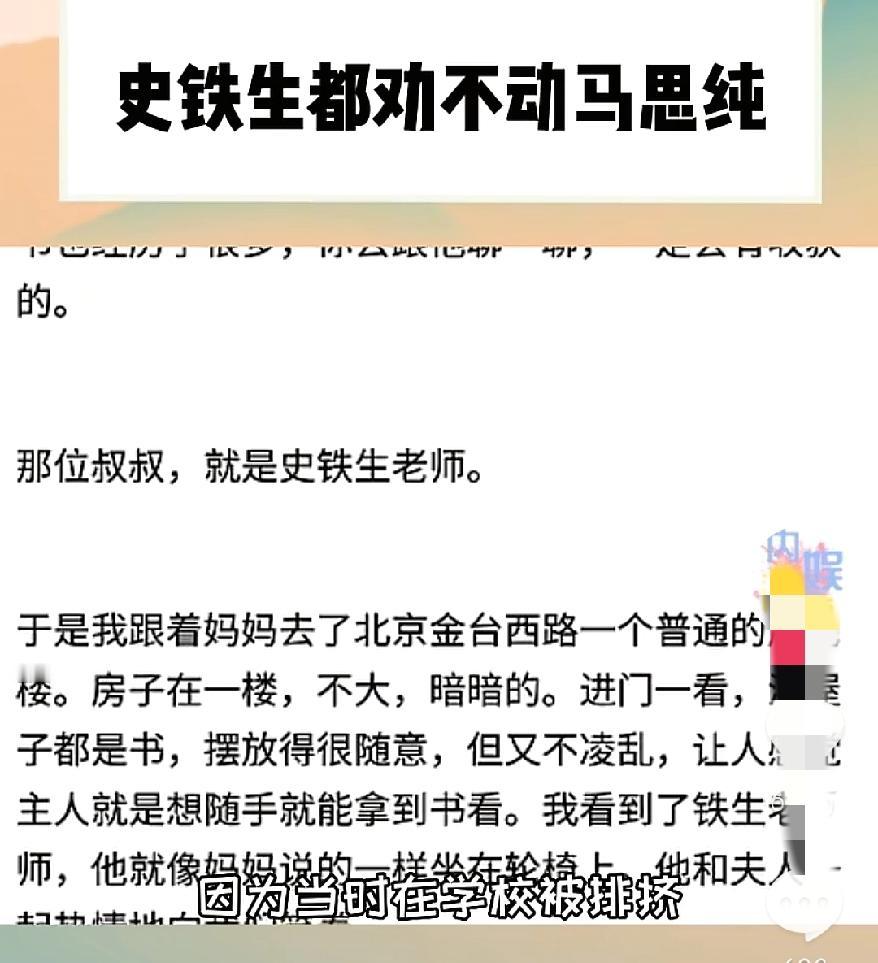当金高银饰演的柳恩中攥着那张泛黄的舞步卡片,看着病床上瘦得脱相的朴智贤(饰千商燕),终于把那句憋了三十年的话砸出来:“你不是要我陪你死,是要我替你活成被记住的样子”——我突然明白,这部被营销号吹成“韩版七月与安生”的剧,根本不是什么友情圣经,而是把女性之间最拧巴的“参照系情谊”扒得明明白白。它笑着讲两个女人的拉扯,哭着藏起关于“自我确认”的终极命题,最后扔给观众一个扎心的问号:你身边那个让你又爱又恨的人,到底是挚友,还是另一个自己?

从11岁开始的“镜像竞争”
剧里的开篇简直是韩式阶级叙事的老熟人:1998年的首尔,半地下室的柳恩中啃着干硬的打糕写作业,头顶的灯泡忽明忽暗;高档公寓里的千商燕对着钢琴哭,指尖被妈妈敲得发红。这俩能凑到一起,全靠小学班主任的“扶贫式分组”——让成绩好但孤僻的商燕带活泼却偏科的恩中。现在回头看,这哪是帮扶,分明是给两只小兽扔了面照妖镜。

小孩子的竞争从来都带着可爱的幼稚气。恩中羡慕商燕的自动铅笔,就把妈妈织的手套拆了,用毛线给商燕做“独一无二”的笔套;商燕嫉妒恩中总能被爸爸举过头顶,就偷偷把恩中的跳绳藏起来,再“碰巧”拿出自己的新跳绳邀她一起玩。最逗的是校庆演出,两人跳《桔梗谣》,恩中忘动作时商燕故意慢半拍带她,转头商燕摔下台,恩中抱着她往医务室冲,边跑边骂“你怎么比我奶奶还笨”。那时候的羡慕是真的,嫉妒也是真的,但底色是暖的——就像恩中手绘的舞步卡片,边角被商燕磨得起毛,却一直夹在她的钢琴谱里。

可编剧坏就坏在,偏要在这暖底色上划一刀。商燕的哥哥自杀那天,她攥着哥哥给的水果糖跑去找恩中,话没说出口就哭晕过去。等她醒过来,搬家公司已经把家具搬空了。恩中拿着准备好的生日贺卡站在空荡荡的公寓楼下,直到天黑都没等到人。这一别,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把“参照物”突然抽走的恐慌——商燕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伞,恩中失去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多年后恩中在采访里说“那天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像谁一样活着”,这话听着矫情,却是所有女孩都懂的共鸣:我们总在朋友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哪怕那影子是歪的。

抢男人?不,是抢“被认可”的资格
大学重逢那场戏,金高银和朴智贤的演技简直是教科书。在摄影社的招新会上,恩中举着相机拍落日,镜头里突然闯进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手一抖,照片糊了——商燕站在逆光里,穿着白衬衫,比高中时更耀眼。两人对视三秒,然后同时尖叫着扑过去,眼泪混着笑声,活像两只久别重逢的小兽。那时候她们都以为,错过的时光能补回来,却忘了镜子一旦裂过,再拼起来总会有缝。

关于“抢学长”的戏码,网上骂商燕“绿茶”的人不少,但我越看越觉得,金尚壑学长根本就是个工具人。恩中喜欢他,是因为他夸她的摄影作品“有生命力”——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半地下室的出身没什么可自卑的;商燕盯着他,是因为他是系里的风云人物,拿下他,就像拿下钢琴比赛冠军一样,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你看,她们争的从来不是男人,是“我是不是足够好”的答案。

那场“网友变现翻车”的戏能笑死人也能气死人。商燕用小号跟学长聊了一年摄影,转头就把恩中的相机电池藏起来,让她错过和学长的约定;恩中知道后,故意在学长面前说商燕“讨厌芒果”,害得商燕在约会时对着芒果甜品强装镇定。最后真相败露,学长夹在中间一脸懵,这俩姑奶奶倒先吵了起来:“你就是怕我比你先被人喜欢!”“你明明知道我没人疼,还抢我的机会!”——听听,这哪是争风吃醋,分明是把这些年的委屈和不甘都倒了出来。
其实从商燕藏起电池的那一刻起,她们的友情就变味了。不是因为男人,是因为长大的世界里,“被认可”的名额太有限。半地下室的恩中靠着努力能拿到奖学金,公寓楼的商燕却发现,再优秀也换不来父母的一句夸奖。她们就像两根缠绕生长的藤,彼此借力,也彼此绞杀,而那根叫“金尚壑”的竹竿,不过是让她们绞得更紧的借口。

当“参照物”变成“绊脚石”
如果说大学的竞争是小打小闹,那职场上的交锋就是真刀真枪。恩中成了编剧,写的女性题材剧本被业内夸“有温度”;商燕成了制片人,凭着狠辣的手段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两人重逢在投资方的会议室,恩中抱着剧本,商燕靠在真皮沙发上,手指敲着桌面:“柳编剧的作品很有潜力,不过需要改改,更符合市场。”

接下来的剧情,简直是职场女性的噩梦复刻。恩中把打磨了两年的剧本交给商燕提意见,转头就看到商燕以“原创制作人”的身份站在项目发布会上;恩中去找她理论,商燕坐在落地窗前,背对着她说:“你知道投资方为什么选我吗?因为你太天真,总觉得情怀能当饭吃。”最扎心的是,商燕改的剧本里,把女主角的半地下室背景改成了公寓楼,把她的乐观改成了敏感——她根本不是在改剧本,是在把恩中的人生,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很多人骂商燕“坏得彻底”,但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太多女性的困境。她在酒局上被投资方占便宜时,只能笑着灌自己酒;她妈妈打电话来,永远只问“什么时候嫁个有钱人”;她深夜在办公室吃泡面,看着恩中和家人视频的朋友圈,突然把泡面扔了。她那句“讨厌你这么完好的样子,你要是像我一样被毁掉就好了”,听着恶毒,其实是绝望——她一辈子都在追赶恩中的“完好”,却忘了自己也曾是那个会给朋友做笔套的女孩。

恩中的反击也很解气。她没有哭闹,而是把商燕改剧本的证据整理好,匿名发给了行业媒体,又带着原剧本找到了另一家投资方。项目重启那天,商燕的公司股价暴跌,她在停车场拦住恩中,两人对视良久,商燕说“我输了”,恩中却哭了:“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啊,从一起跳《桔梗谣》的小女孩,到职场上的死对头,她们到底是哪里走偏了?

用死亡完成的“终极捆绑”
十年没联系的空白,被一通医院的电话填满。恩中赶到病房时,差点没认出商燕——曾经光彩照人的制片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化疗把头发都掉光了。商燕递给她一张瑞士的机票,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陪我去安乐死,怎么样?”

这个请求简直是道德绑架的天花板。恩中的老公劝她“别趟这浑水”,她的编剧搭档说“她当年那么对你,你没必要”,但恩中还是收拾了行李。不是因为圣母心,是因为她知道,商燕这招“将军”,她躲不掉。陪商燕去瑞士,就等于承认这个女人在自己生命里的分量;不去,她这辈子都会活在“我是不是太冷血”的愧疚里。商燕太了解她了,就像她了解商燕一样。
瑞士的雪山很美,美得像她们小时候的梦境。商燕坐在轮椅上,恩中推着她,两人终于说起了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商燕说当年藏跳绳,是因为“看到你爸爸举着你,我嫉妒得发疯”;恩中说当年故意说错芒果的事,是因为“你总那么耀眼,我想让你出一次丑”。她们在湖边吃着童年味道的打糕,商燕突然哭了:“我抢你的剧本,是怕你越来越优秀,我就彻底被你甩在后面了。”恩中摸着她的头,就像小时候那样:“傻瓜,我从来没把你当对手。”

但编剧没给她们俗套的和解。安乐死签字前夜,商燕给了恩中一个信封,说“等我走了再看”。第二天,商燕穿着最喜欢的裙子,握着恩中的手,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恩中打开信封,里面没有道歉信,只有一张泛黄的舞步卡片——是她当年给商燕画的那张,背面写着:“恩中,没有你,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

比友情更复杂的“自我确认”

很多人说这部剧讲的是女性友谊,我却觉得,它讲的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自我确认”之路。柳恩中和千商燕,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闺蜜,而是彼此的“活体坐标”——通过对方的存在,确认自己的位置;通过和对方的竞争,找到自己的边界;通过对对方的爱恨,看清自己的软肋。
商燕的一生,都在通过恩中确认“我值得被爱”。她抢学长,是想证明自己不是没人喜欢的孩子;她抢剧本,是想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境的废物;她求恩中陪她死,是想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被一个人在乎。而恩中的一生,也在通过商燕确认“我足够优秀”。她努力学习,是想跟上商燕的脚步;她坚持写有温度的剧本,是想守住自己和商燕最初的样子;她陪商燕去瑞士,是想确认自己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这就是关系或者说是人性最拧巴也最真实的地方:我们既想成为对方,又想超越对方;既怕失去对方,又怕被对方吞噬。就像剧里反复出现的镜子意象——商燕家里的穿衣镜,恩中摄影包里的反光板,甚至是她们手机里的自拍镜头,都在暗示着这种“镜像关系”。我们身边都有这样一个人,她的优点是你的目标,她的缺点是你的安慰,她的成功让你骄傲,她的失败让你窃喜——别否认,这不是坏,是人性。
这部剧的深层含义,从来不是“友情需要包容”,而是“你终要学会,不通过别人的镜子,也能看清自己”。商燕到死都没明白这个道理,她用死亡完成了对恩中的终极捆绑;而恩中在商燕死后,把那张舞步卡片和自己的剧本放在一起,她终于明白,自己的价值,不是“比商燕更完好”,而是“我就是柳恩中”。
©Mark电影范供稿。
(文中部分资料、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