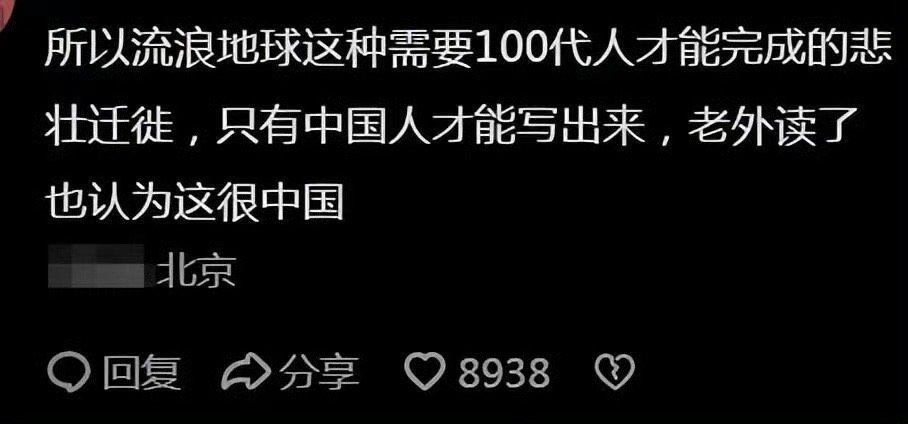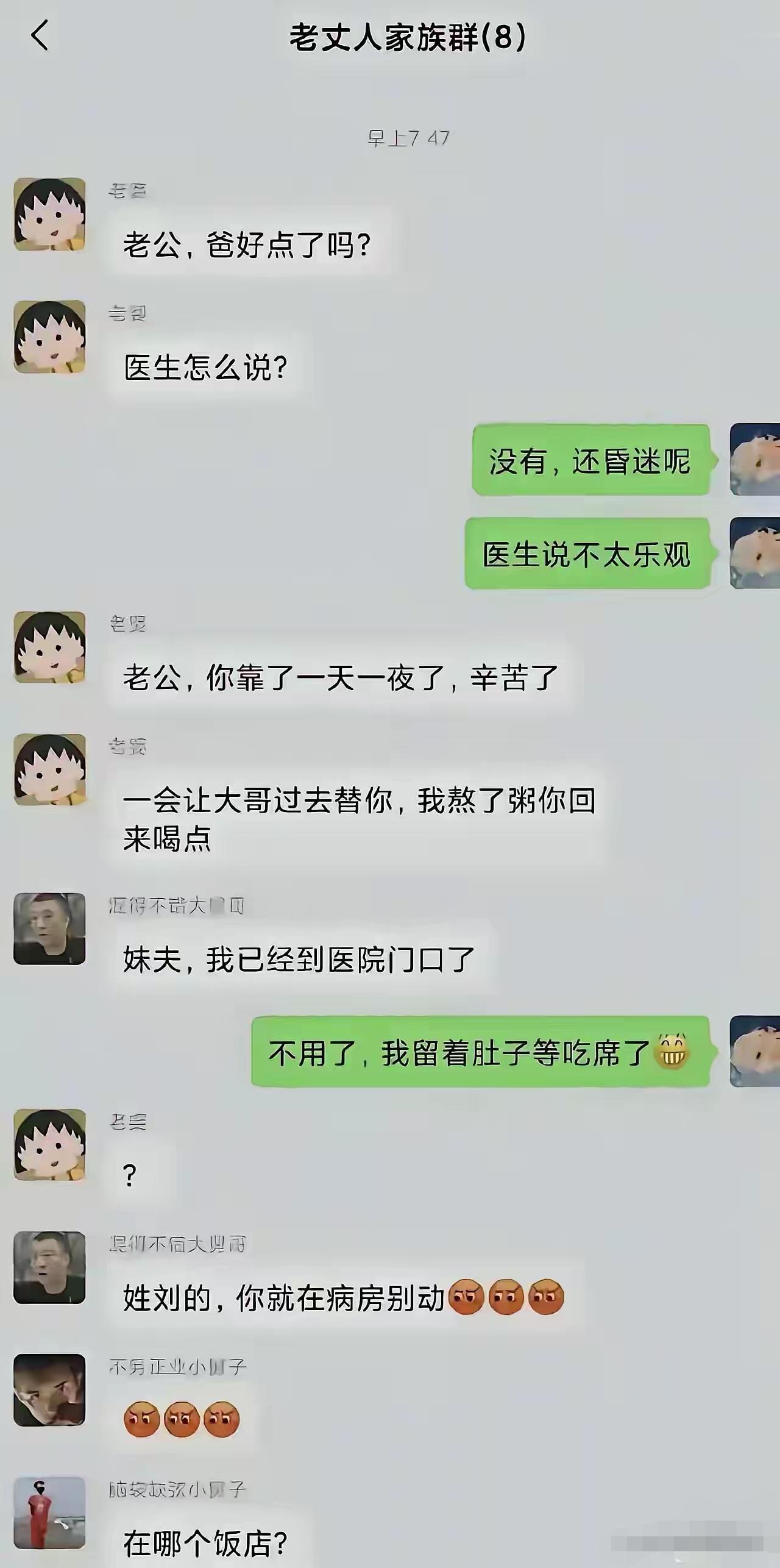那帮洋人等着看笑话
1905年的北京城,空气里不仅仅有煤烟味,还有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大清朝的日子不多了,这点哪怕是街边卖烤红薯的老头都感觉得到。朝廷里的老爷们还在勉强维持着体面,但在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眼里,这体面比窗户纸还薄。

就在这个时候,京张铁路的消息传出来了。
这不仅仅是一条路。这是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一场比赛。英国人说,这路经过的地方不仅有我们的利益,还得用我们的工程师。俄国人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说长城以北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除了我们谁也别想修。双方僵持不下,唾沫星子横飞,最后竟然达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妥协:既然我们要不成,你们也要不成,那就让中国人自己修。
这主意损透了。
当时的中国铁路工程师在洋人眼里是个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让一个厨子去造原子弹。英国的《泰晤士报》毫不客气地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这种复杂的地形,这种高难度的工程,中国工程师能修出来的几率基本为0。他们甚至私下里开了盘口,赌中国人什么时候会哭着回来求他们接手。
这时候,袁世凯把一个人推到了台前。这人个子不高,留着那时候必须留的胡子,眼神很沉。他叫詹天佑。

洋人们听到这个名字,反应很一致:他是谁?哦,那个耶鲁毕业的。耶鲁毕业又怎么样,他修过这种要在悬崖峭壁上打洞的铁路吗?他手里有先进的盾构机吗?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施工队吗?
都没有。
詹天佑接这个活的时候,手里只有五百万两银子。听着挺多,但你得看这路要往哪儿修。从北京到张家口,中间横着军都山,地形复杂。关沟那一段,海拔落差大得吓人,每走几步就得往上爬一截。
所有人都觉得詹天佑疯了,或者说,袁世凯疯了。
詹天佑没疯。他只是拿了一张地图,一支笔,站在南口寒风凛冽的工地上,看了看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他没说话,也没发誓,更没有对这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外国记者发表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紧了紧衣领,转头对自己那几个同样一脸忐忑的助手说了一句:走,上山看看。
这一走,就是四年。
被送去蛮荒之地的孩子
时间回到1872年。
那时候的广东南海,海风里带着咸腥味。十二岁的詹天佑正在家里读四书五经,但他爹詹兴洪最近很烦。朝廷搞了个“留美幼童”的计划,要选一批聪明的孩子送到那个叫美利坚的地方去读书。
现在人听起来这是好事,公费留学,还是去美国。但在当时,这简直就是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在老百姓眼里,美国那是蛮荒之地,那里的人茹毛饮血,没准还吃小孩。更重要的是,这一去就是十五年。十五年啊,回来以后这孩子还认得爹娘吗?还认得祖宗吗?
没人愿意去。朝廷派人到广东招生,结果应者寥寥。大家躲都来不及。
詹兴洪本来也不想让儿子去。但这里有个关键人物,叫谭伯村。他是詹兴洪的好朋友,也是个见过世面的商人。他对詹兴洪说,你这儿子聪明是聪明,但你要让他考科举,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什么时候是个头?洋人的东西,虽然奇技淫巧,但将来未必没用。你去,我把女儿许配给你儿子。
这买卖划算。
詹天佑就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下,被打包送上了去上海的船,然后换乘轮船,横渡太平洋。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群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孩,在旧金山下船的时候,引起了多大的围观。美国人看他们像看外星人,他们看美国人也像看怪物。
詹天佑被分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威斯海芬,寄宿在一个叫诺索普的小学老师家里。这老师人不错,没把詹天佑当怪物,反而对他那一头长辫子很感兴趣。

在这里,詹天佑干了一件让后来很多历史学家都津津乐道的事:打棒球。
现在的资料里,还能找到詹天佑拿着棒球棍的照片。他不是那种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他在球场上跑得飞快,甚至还有个外号叫“球王”。这让他在美国同学里混得很开。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詹天佑的脑子灵活,身体协调性好,而且适应能力极强。这一点,在他后来在悬崖上测绘的时候,起到了救命的作用。
1878年,詹天佑考进了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
这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一起留学的很多人,选的都是法律、军事或者外交。因为这些学科听起来高大上,将来回国好做官。土木工程?那是工匠干的活,是下九流。在大清的价值观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修路架桥,那是劳力。
但詹天佑选了。他主攻铁路。
他在耶鲁的成绩单现在还能查到,数学极好。这很重要。因为几十年后,当他在京张铁路上计算那个著名的“人”字形轨道时,靠的就是这种扎实的数学功底。任何一点计算失误,火车就会倒着滑下山谷,变成一堆废铁。
1881年,詹天佑毕业了。他是全班第一名。
按理说,这样的人才回国,朝廷应该敲锣打鼓地欢迎,然后委以重任。毕竟花了那么多银子培养,现在终于到了摘果子的时候。
然而,现实给了詹天佑结结实实的一巴掌。
你们是回来干什么的?
詹天佑他们回国的时候,气氛很不对劲。
朝廷里的保守派发难了。他们说这帮留学生在美国不务正业,剪辫子(其实大部分没剪),穿西装,信基督教,简直就是一群忘了祖宗的假洋鬼子。朝廷一听,既然这样,那就都撤回来吧。
于是,詹天佑还没来得及在美国实习几天,就被强行召回。
船靠岸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没有来接的人。他们被关在上海的一个书院里,像犯人一样被看管起来。官员们看着这帮穿着洋装、说着英语的年轻人,眼神里充满了厌恶和怀疑。

詹天佑的耶鲁毕业证,在这些官员眼里,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
分配工作的时候,没人问詹天佑学的是什么。管你学的是土木工程还是物理学,统统乱点鸳鸯谱。詹天佑被分到了福州船政学堂。
去教书。
让一个耶鲁顶尖的土木工程毕业生,去教一帮预备海军怎么开船。这事怎么看怎么荒诞。但詹天佑没抱怨。他收拾行李,去了福州。
他在那里待了好几年。教英语,教数学,偶尔也教教怎么看海图。这段日子对他来说不仅是浪费,简直是折磨。他看着那些生锈的军舰,看着那些吸鸦片的水手,心里大概明白,这大清朝的病,根源在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工业基础的薄弱,不是靠几艘船能治好的。
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

詹天佑当时就在“扬武”号旗舰上。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屠杀。法国人的军舰无论是火力还是机动性,都碾压福建水师。
詹天佑虽然不是战斗人员,但他目睹了全过程。他看着身边的战友被炮弹撕碎,看着自己服役的军舰燃起大火,慢慢沉入江底。他在水里扑腾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仅仅是求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输?
是因为船不行吗?是因为炮不行吗?
不,是因为根基不行。工业不行,交通不行,后勤不行。
这场海战之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他意识到,在海上漂着救不了中国,得回到陆地上来。得修路。只有路通了,血脉才能通。
这时候,机会来了,虽然是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机会。
那个叫金达的英国人
两广总督张之洞要修铁路,需要人。詹天佑就被推荐过去了。
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重用。在那个年代,中国的铁路上全是外国工程师。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他们把持着所有的技术岗位。中国工程师?顶多就是个翻译,或者是工头。
詹天佑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是英国工程师金达。

金达这人技术不错,但也傲慢。他负责修津卢铁路。詹天佑被派到他手下当实习工程师。一开始,金达根本没正眼看过这个个子不高的中国人。在他看来,詹天佑就是个那个年代常见的、唯唯诺诺的衙门小吏。
直到有一天,滦河大桥出事了。
滦河这地方,水流急,河床全是沙。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试过了,桥墩就是打不下去。打下去就歪,歪了就倒。金达也愁得头发都要掉了。

这时候,詹天佑站了出来。他说,我有办法。
金达斜着眼睛看他:你有办法?你也懂打桩?
詹天佑没跟他废话。他没有用洋人那种传统的打桩法。他研究了很久,提出了一种新的气压沉箱法。简单说,就是利用气压把水排开,让人到底下去挖泥,直接把地基坐到岩石层上。
这在当时是很前卫的技术,而且风险很大。工人们不敢下去。詹天佑二话不说,自己先下去了。
他在那浑浊、高压的沉箱里待了很久,亲自指挥定位。最后,桥墩稳稳地立住了。
这一仗,把金达打服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中国人不仅英语说得比他还溜,技术上也是个硬茬。从那以后,金达开始重用詹天佑。
但这只是小试牛刀。真正的修罗场,在很多年后的京张铁路。
关沟的死局
回到1905年的那个冬天。
詹天佑接手了京张铁路。五百万两银子,四年时间。
线路怎么走?
最难的一段是关沟。从南口到八达岭,这一段路,直线距离不到二十公里,但海拔升高了五六百米。两边全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乱石岗。

当时的火车,爬坡能力很差。一般来说,千分之二十五的坡度就是极限了。也就是说,每一千米路,升高二十五米。再高,车轮就会打滑,车头就会趴窝。
可是关沟这一段,如果不绕远路,坡度达到了千分之三十三。
很多外国专家来看过,看完都摇头。他们建议绕路。绕哪儿呢?绕得远得没边了,成本至少增加几百万两,工期得拖好几年。詹天佑没钱,也没时间。
他必须在千分之三十三的坡度上把路修通。
怎么修?
詹天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绕路,硬上。
但他不是蛮干。他先是用脚把关沟的每一寸土地都丈量了一遍。那时候测绘仪器很笨重,风又大。他和助手们扛着仪器,在悬崖上爬上爬下。为了一个数据,有时候得在风口里站好几个小时。
他的日记里没有写什么辛苦,全是数字。哪个标高是多少,哪块石头的硬度是多少。
他发现,如果直接爬,肯定不行。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长坡变成短坡,中间加平路缓冲。但这还不够。
必须得打隧道。
居庸关隧道,八达岭隧道。这又是两个拦路虎。尤其是八达岭隧道,一千多米长。在那时候,没有盾构机,全靠人工拿凿子凿,拿炸药炸。如果从两头往中间挖,得挖到猴年马月去。

詹天佑想出了那招著名的“竖井法”。
他在隧道中间的山顶上,打了两个直井下去,一直打到隧道的高度。然后从井底向两头挖。这样,加上原本的两头,就有六个工作面同时在挖。

这想法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登天。
首先,你怎么保证这六个面最后能对上?万一挖歪了,中间错开了,那可就成了国际笑话了。
詹天佑靠的是计算。一遍又一遍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他在井口吊了重锤,用来校准方向。每一米掘进,都要重新测量。
工人们不懂什么几何学,他们只知道,詹大人说往哪挖,就往哪挖。
结果呢?最后贯通的时候,几个工作面的误差,只有极小的一点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洋人听说了这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人字形的急转弯
隧道解决了,坡度还是个大问题。
千分之三十三。火车怎么爬?
这时候,詹天佑拿出了他的杀手锏:人字形铁路。
这其实不是詹天佑发明的,这种设计在美洲的一些矿山铁路里用过。但在干线铁路上用,而且是用在这么险要的地方,绝对是大胆的尝试。
原理很简单:火车爬不动了,就停下来,车尾变车头,倒着走另一条岔道继续爬。就像人爬楼梯一样,之字形往上走。

但实施起来非常复杂。你需要两个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到了人字形的尖端,前面的车头变成了后面的推,后面的车头变成了前面的拉。
这对调度、配合、路基的强度都有极高的要求。
而且,因为有两个车头,牵引力大了,但车钩的受力也大了。万一车钩断了,那就是车毁人亡。詹天佑又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铁路人管它叫“詹氏挂钩”(虽然不是他发明的,但他推广有功)。
在施工的那段时间里,詹天佑基本上就住在工地上。他跟工人们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工棚。那时候的工棚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詹天佑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从来不搞特殊。
有一次,工程队遇到了一块巨硬的花岗岩。炸药炸不开,钢钎打卷了。工头都要哭了,说这石头是不是成精了。詹天佑跑过去,摸了摸石头,研究了纹理,然后告诉他们在哪里打眼,用多少药量。
轰的一声,石头裂了。
这不是玄学,是地质学。
并没有那么多掌声
1909年,京张铁路全线通车。

比计划提前了两年。
省下的银子,不仅还了贷款,还给朝廷发了一笔小财。
通车典礼那天,非常热闹。张家口的百姓倾巢出动,都要看看这喷火的家伙。官员们来了,穿着朝服,在那儿互相恭维。外国公使也来了,虽然脸色不太好看,但也得硬着头皮说几句“Congratulation”。
詹天佑站在人群里,表情很平静。
他没有发表长篇演讲。他只是觉得累。这四年,透支了他太多的精力。
有人问他,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他可能最想睡个觉。
京张铁路的成功,把詹天佑推上了神坛。他成了“中国铁路之父”。但这个头衔,对他来说,意味着更重的担子。
清朝灭亡了,民国来了。乱世之中,修铁路更难了。军阀混战,今天这个大帅要用车皮运兵,明天那个督军挪用铁路物资,甚至拆毁部分铁轨充作军资。詹天佑不仅要当工程师,还得当外交官,去跟各路神仙周旋,保护铁路资产。
他后来主持修建汉粤川铁路。这工程比京张铁路更大,但也更艰难。不是技术难,是人心难。资金不到位,各省扯皮,贪污腐败。
詹天佑心力交瘁。
1919年,他去了一趟巴黎。去参加远东铁路会议。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分赃大会。他在会上据理力争,维护中国在西伯利亚铁路的权益。
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长期的野外工作,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腹疾。
回国后不久,他在汉口病倒了。
最后的交代
医生告诉他,日子不多了。
詹天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这时候的他,脑子里想的应该不是耶鲁的棒球场,也不是福建海面的炮火,甚至不是京张铁路的人字形轨道。
他在担心汉粤川铁路还没修完。

他在担心中国培养的年轻工程师能不能接上班。
他叫来家人和同事,立下了遗嘱。
这遗嘱很有意思。如果是普通的官员,这时候该交代家产怎么分,或者让子孙后代好好做人。
詹天佑的遗嘱里,大部分篇幅在谈国家大事,谈铁路建设,谈人才培养。他说:“吾死之后,所遗职务,需慎选得人……”
他还特别嘱咐,要把他的技术书籍和图纸都捐给国家。
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走了。享年58岁。
如果他不回来
故事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
如果1881年,詹天佑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美国。凭他的才华,他完全可以在美国的铁路大建设时期混得风生水起。他可能会成为某个大铁路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拿着高薪,住着别墅,周末去打打棒球,过完富足而平静的一生。
没人会指责他。那是人的本能选择。
但他回来了。
他忍受了冷遇,忍受了嘲笑,忍受了倾轧,忍受了风餐露宿。他把自己的才华,全部砸进了中国这片土地里。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笨人吗?当然不是。他是耶鲁的高材生,精明得很。
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片土地上的人,值得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铁路。他相信,只要给他支点,中国人不比任何人差。
在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有一尊詹天佑的铜像。铜像下面,埋葬着他和夫人的灵柩。

那是离“人”字形铁路最近的车站。
每天,列车从那里呼啸而过。现在的火车,时速已经是当年的十倍、二十倍。现在的中国,高铁网络遍布全国,穿山越岭如履平地。
如果你有机会坐着高铁经过青龙桥,哪怕只有一瞬间,不妨往窗外看一眼。
那个留着胡子的小个子男人,可能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秒表,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看着这一切。
他赢了那场赌局。赢得彻底,赢得漂亮。
而且,这回再也没有人敢笑话了。
免责提示:本文基于公开历史资料与技术文献整理,部分细节为叙事化演绎,仅供科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