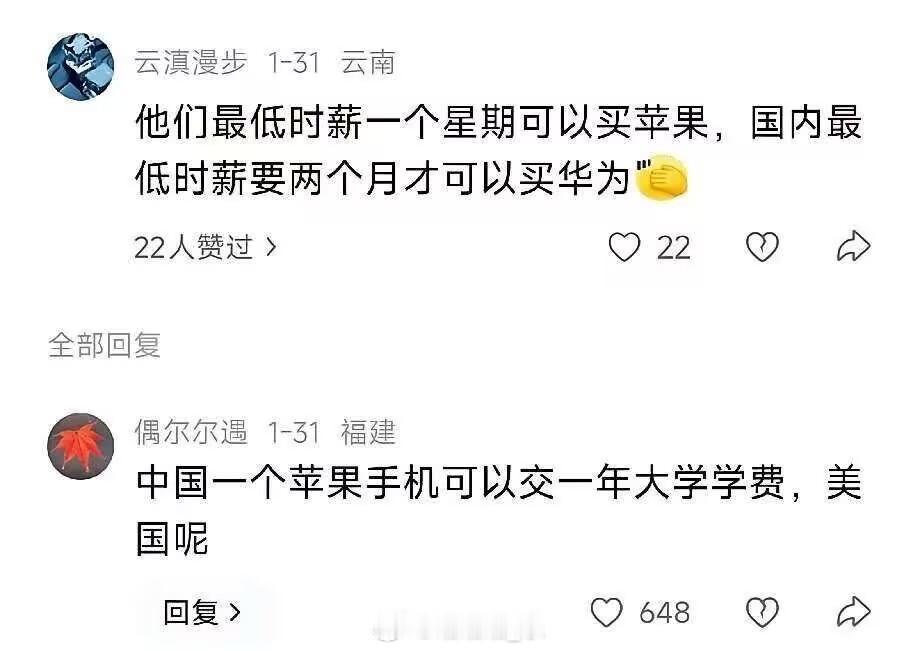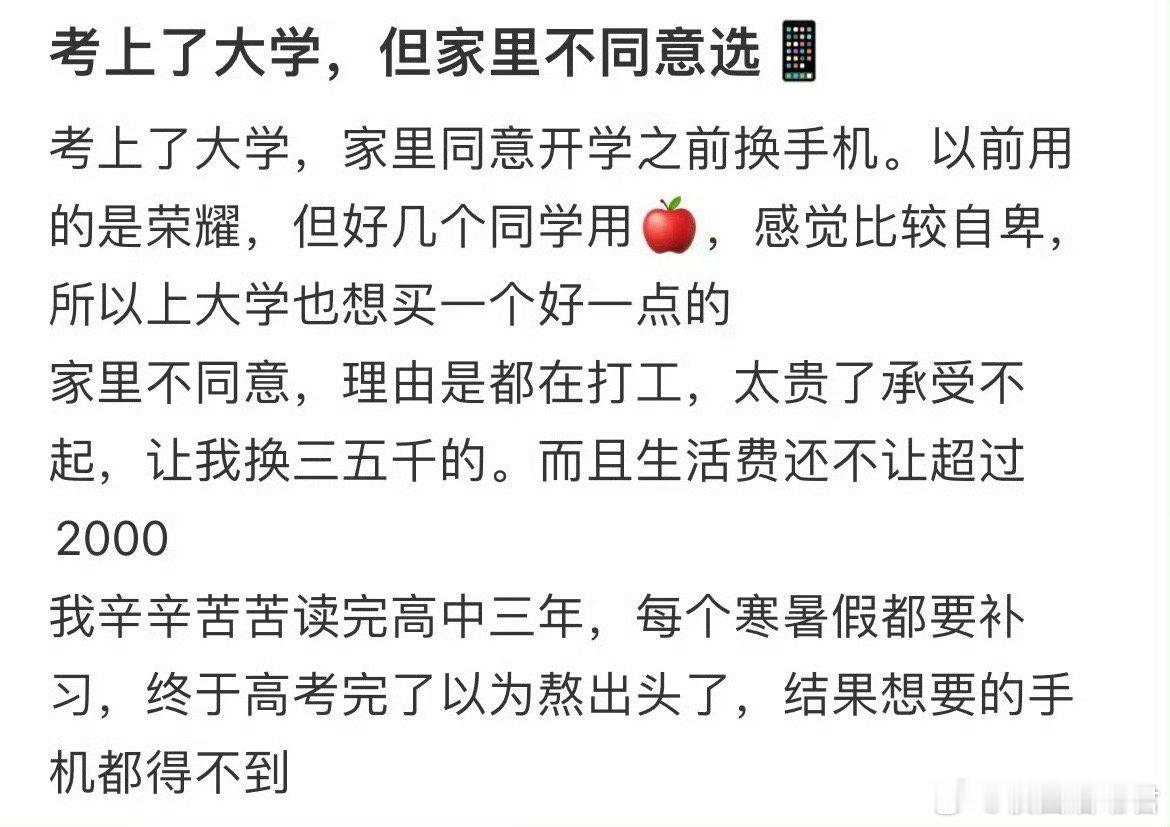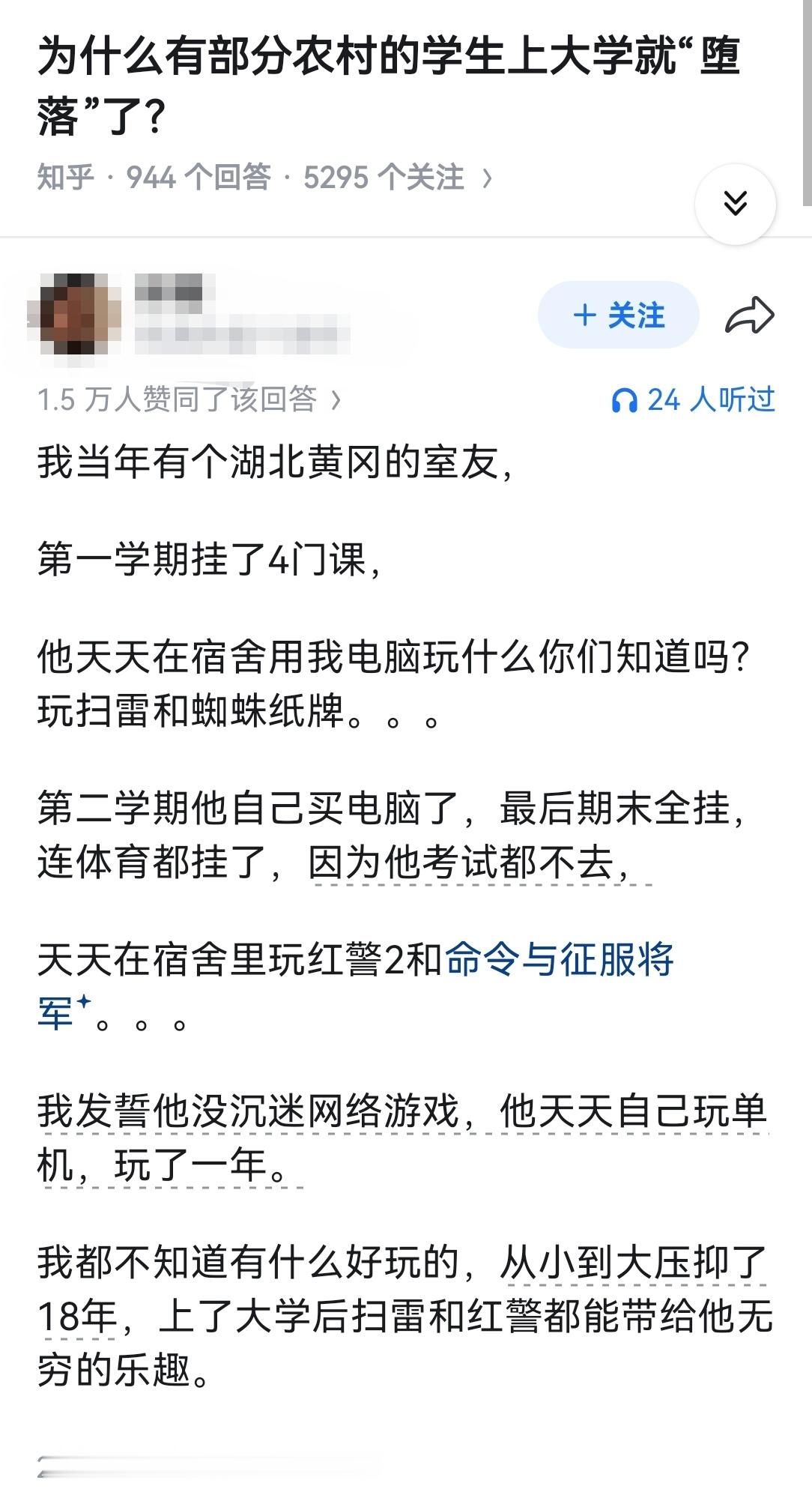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雨下得很大。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和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二叔拄着拐,一瘸一拐地从泥路那头挪过来,蓑衣滴滴答答往下滴水。
“娃,中了?”他的声音哑得厉害。
我把通知书递过去。他那只因早年工伤而扭曲变形、使不上劲的左手,在衣服上反复擦了好几遍,才用右手接过去。他就那么站着,在瓢泼大雨里,低着头,看了很久。雨水把纸打湿了一角,他慌忙用袖子去捂,笨拙得像护着一块脆弱的琉璃。
“好,好……”他反复念叨着,抬起头时,眼圈通红,脸上却是我从未见过的光亮,“咱家……出大学生了。”
回到家——那间属于二叔的、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他小心翼翼地把通知书压在炕席底下,用一块砖头压好。然后,他翻出了家里唯一一个还算体面的布包,拍了拍灰,递给我。
“换上你最好那件衣裳。”他说,语气不容置疑,“咱出去一趟。”
“二叔,去哪?”我心里隐隐猜到,喉咙发紧。
“借钱。”他吐出两个字,弯腰从床底拖出一个磨得发亮的旧铁盒,打开。里面是零零散散的毛票,最大的面额是十块。他数了一遍,又数一遍,总共三百二十七块八毛。
“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差得远。”他自言自语,然后把铁盒盖上,放回原处,仿佛那笔巨款与他无关。他看向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心:“走,叔带你,挨家挨户借去。”
七年前,爹在矿上出事,人没抬回来,就赔了一笔抚恤金。那钱,在我爹坟头的土还没干透的时候,就被我娘攥在手里,成了她改嫁的嫁妆。她走的那天,也是下雨,没回头看我一眼。
我当时十岁,像个被遗弃的物件,站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是二叔,拖着那条残腿,把我领回了他的小屋。
二叔年轻时在镇上砖厂干活,被机器绞了左手,废了,腿也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活。厂里赔了点钱,早用光了。他一个人过,日子紧巴得响叮当。多我一张嘴,难上加难。
我记得刚来那会儿,晚上饿得睡不着。二叔默不作声地起来,在灶台边摸索半天,给我煮了一碗清汤挂面,卧了一个鸡蛋。他自己就着咸菜,喝面汤。
“娃,别怕,有叔在,饿不着你。”他当时就这么说,声音平平淡淡。
为了这句话,他拖着残躯,去给人家看果园,守鱼塘,编竹筐,什么零碎活都接。钱少,活累,但他从没让我辍学。村里有人劝他:“一个瘸子,养自己都费劲,还带个拖油瓶?让他早点出去打工是正经。”
二叔总是闷着头,“吧嗒吧嗒”抽他的旱烟,半晌才回一句:“他爹临死前,最惦记娃的学业。我得对得起我哥。”
这一养,就是七年。我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二叔的背,一年比一年驼得厉害。
第一站,是村东头的堂伯家。堂伯在镇上开小卖部,算是村里日子过得最滋润的。
二叔让我在门外等,他自己拄着拐进去。我隔着窗户,看见堂伯坐在沙发上剔牙,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二叔佝偻着背,脸上堆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近乎卑微的笑容,双手递上我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嘴里说着什么。
堂伯瞥了一眼通知书,没接,继续剔牙,声音透过窗户缝传出来:“德华啊,不是我说你,你自己啥情况不清楚?供个大学生?开玩笑嘛!那是个无底洞!再说了,女娃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人。”
二叔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收回通知书,手有点抖,但还是努力维持着语气:“娃争气,考的是好大学,将来有出息,肯定忘不了您的好……”
“得了吧!”堂伯不耐烦地挥手,“我这小本生意,周转都难。没钱,真没钱。你们去别家看看吧。”
二叔嘴唇嚅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慢慢转过身,拄着拐走出来。看到我,他努力扯出一个笑:“没事,这家不行,咱去下一家。”
第二家,是村西的远房婶子。婶子倒是客气,让我们进了屋,还倒了水。她拿着通知书看了又看,叹了口气:“娃是真出息。可是德华啊,你也知道,我家那小子去年结婚,彩礼钱还欠着债呢……实在拿不出啊。”
第三家,第四家……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村子。
冷言冷语是家常便饭。“哟,瘸子还想培养个凤凰出来?”“借钱?拿什么还?用你那条瘸腿还?”“女娃娃,读个师范出来当老师还行,读这专业,将来工作都难找!”
也有表面客气,实则推诿的。“真不巧,钱刚存了定期。”“哎呀,当家的不在,我做不了主。”
每被拒绝一次,二叔的背就好像更弯下去一点。但他从不气馁,总是整理一下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清清嗓子,带着我走向下一家。他一遍遍重复着:“我侄女,考上了XX大学,将来一定有出息,这钱我们肯定还,砸锅卖铁也还……”
雨水时停时下,他的裤腿和我的布鞋,早已被泥浆糊满。那封录取通知书,被他紧紧捂在怀里,怕被雨淋湿。
走到村尾五保户陈奶奶家时,天都快黑了。陈奶奶八十多了,耳背,眼睛也不好。二叔大声说了好几遍,她才听明白。
她颤巍巍地起身,走进里屋,摸索了半天,拿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一共一百二十块钱。
“娃考上大学,好事,大好事。”陈奶奶把钱塞到我手里,她的手干枯得像老树皮,却异常温暖,“奶奶没多少,一点心意,别嫌少。好好读,给咱村争光。”
我捏着那还带着老人体温的钱,眼泪“唰”就下来了。这是今天收到的第一笔,也是唯一一笔“借款”。
二叔也背过身去,用他那只好手,用力抹了把脸。然后,他朝着陈奶奶,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您老,这钱……我们一定还。”
回去的路上,我们沉默着。布包里,除了陈奶奶的一百二十块,只有另一户实在抹不开面子的邻居借的五十块。离那笔昂贵的学费,仍是天文数字。
晚上,昏暗的灯光下,二叔对着那寥寥的一百七十块钱,发了很久的呆。我煮了粥,叫他吃饭。
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娃,你怪叔没本事不?”
我拼命摇头,眼泪又涌上来:“二叔,没有你,我早就不知道在哪儿了。这学……我不上了,我明天就去找活干,我养你。”
“放屁!”二叔猛地一拍桌子,很少见他这么激动,“必须上!这学必须上!你爹要是知道你能上大学,在地下都能笑醒!”他喘了口气,语气缓和下来,却更加坚定,“钱的事,你别管。叔有办法。”
第二天一早,二叔不见了。晌午他才回来,眼里布满血丝,但神情却松快了些。他告诉我,他天没亮就走着去了镇上,找了当年砖厂的老领导,磨了半天,人家答应做担保,帮他去信用社试试申请助学贷款。
“还有,”二叔从怀里掏出一个存折,很旧了,“这是叔这些年,一点点攒的,本来想……算了,你看看。”
我打开,里面每隔几个月,有一笔很小的存入记录,几十块,一百块,最多一次三百。最后一笔,是前天存的,五十块。余额,两千一百块。这恐怕是他全部的积蓄,是他为自己那条残腿、为未来某个万一,准备的最后保障。
“加上这个,咱们再想想办法,差不离了。”二叔说,“镇上王书记听说咱家的事,说可以帮忙申请贫困生补助。还有,你高中班主任也说了,学校有笔奖金给考上重点大学的……”
希望,像穿透厚重乌云的一缕光,艰难地挤了进来。
接下来的日子,二叔更忙了。助学贷款手续繁琐,他一遍遍往镇上跑,不识字,就求人帮忙看,解释。他赔着笑脸,说着好话,只为尽快把手续办下来。
同时,他接下了帮人看守夏季西瓜地的活。晚上就住在瓜地的窝棚里,防着有人偷瓜。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但他一守就是一个夏天。
我则拼命找一切能做的短期工,发传单,帮餐馆洗碗,去辅导班做助教……每一分钱都攒起来。
录取通知书上要求的报到日期一天天临近。
终于,在开学前一个星期,所有的钱,像用无数辛酸、汗水、尊严和希望凑成的碎片,艰难地拼凑齐了。助学贷款批下来了,贫困生补助到了,学校的奖金发了,加上二叔的积蓄、我打工的钱,以及那永远不能忘的一百七十块“借款”。
交完费的那天,我和二叔去镇上的小馆子,破天荒地点了一盘红烧肉。二叔吃得很少,一直看着我吃,眼里是欣慰,是如释重负,还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娃,到了大学,别惦记家,别惦记钱。专心读书,跟同学好好处。家里啥都好。”他叮嘱着,“那几家借了钱的,地址和数目你都记好,将来,一分一厘都不能少人家的。陈奶奶的,要第一个还,加利息还。”
我重重地点头,把每一句话都刻在心里。
离家的那天清晨,二叔早早起来,给我煮了鸡蛋,蒸了馒头,用塑料袋装好。他执意要送我到镇上的车站。
班车来了,我上了车,找到靠窗的座位。二叔站在车下,隔着车窗玻璃,用力地向我挥手。晨光中,他佝偻的身影显得那么瘦小,那么孤单,但站得笔直。
车开了,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蜿蜒的村路尽头。
我紧紧抱着行李,里面装着简单的衣物,崭新的课本,还有二叔塞进去的两百块钱“零花”。我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能拿出的所有。
大学四年,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申请了所有能申请的勤工助学岗位,学习永远排在第一位。我记着二叔的话,记着那场大雨中的跋涉,记着陈奶奶手绢包里的温暖,也记着那些冷眼与嘲讽。
它们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每年寒假暑假,我都尽量回去,用打工挣的钱,给二叔买点吃的用的。他总怪我乱花钱,但每次我走,都会发现他偷偷把我给的钱,又塞回我的包里。
大四那年,我因为成绩优异,早早签了南方一家很好的公司。拿到第一笔实习工资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那个泛黄笔记本上的记录,把陈奶奶和另外那户邻居的钱,连本带利寄了回去。汇款单附言里,我工工整整地写着:“侄女林溪,大学已毕业,工作顺利,感谢您当年的雪中送炭。祝您身体健康!”
后来,我的工作慢慢稳定,收入也好了起来。我把二叔接到了城里。起初他死活不肯,说不习惯,怕给我添麻烦。我骗他说我工作忙,需要他帮我看看家,他才勉强同意。
现在,二叔住在我的小房子里,每天下楼和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下下棋,晒晒太阳。他的腿脚还是不便,但脸色红润了许多。我给他买了个智能手机,教他视频通话。他最喜欢和我小时候的邻居、陈奶奶的孙子视频,一遍遍跟人家说:“我家溪溪,现在可厉害了……”
他依然节俭,一个塑料袋用了洗,洗了再用。但我给他买的新衣服,他也会高兴地穿上,遇到老伙计,会“不经意”地说:“闺女买的,非让穿。”
那个曾经带他受尽白眼的布包,还放在他衣柜的底层,里面装着那张早已泛黄、但被塑封保存好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以及一个更旧的、字迹歪斜的账本。
有时夜深人静,我加班回家,看到二叔戴着老花镜,就着台灯,轻轻摩挲着那个布包,我会悄悄退出去,不去打扰他的回忆。
爹娘给了我生命,但二叔,用他的残躯和脊梁,为我重新撑起了一片天,让我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光。 那场大雨中的借钱之旅,是我人生最苦涩也最珍贵的一课,它教会我感恩、坚韧与担当。
亲情,有时与血缘无关,它是在绝望处伸出的那只有力的手,是在风雨中为你撑起的那把破旧的伞,是倾其所有、也要把你推向更广阔世界的笨拙而伟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