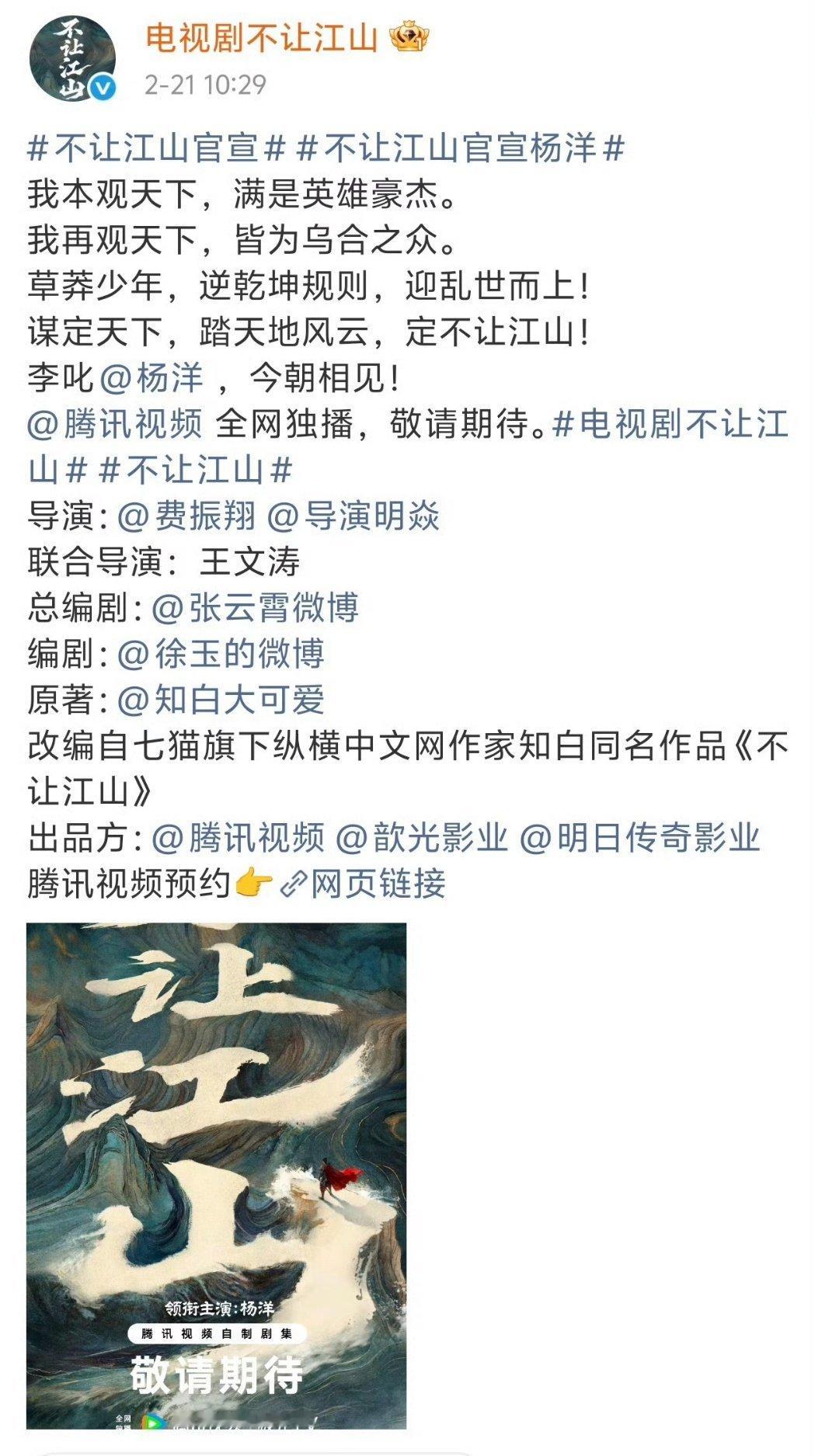从影片本体出发,《星河入梦》依然是今年春节档最值得讨论的作品之一,因为它不仅是韩延在工业规模上的重要尝试,也是他过去创作中现实线与奇幻线的一次同场。这是他创作路径上的阶段性跃迁,也是证明导演纵深能力的重要节点。
作者:小杜
编辑:倪兰
版式:王威

在今年的春节档里,《星河入梦》并没有获得太多声量,但如果只从票房或热度来判断它的价值,反而会错过一件更关键的事——这是一部必须回到导演本人才能真正理解的电影。因为在今年所有新片之中,它几乎是惟一呈现出清晰作者脉络的作品,而这条脉络,从韩延过去十年的创作系统就已经悄悄铺开。
作为中青代最具稳定创作力的导演之一,韩延在现实题材领域构建了清晰的作者路径。他从个体经验走向家庭系统,再走向生命哲学,也逐步建立起一种温柔克制的叙事方法。与此同时,他并非只属于现实主义序列,韩延的奇幻能力始终在暗处生长,只是缺少一个足够大的类型容器将其完全释放。
而《星河入梦》的出现,也让他的能力得以释放。它既继承了现实线中对人物情绪的敏锐捕捉,又让奇幻线的视觉野心得到全面释放,因此,这部电影的讨论价值,在于它如何让韩延的创作跨度第一次以工业规模被看见。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星河入梦》的形态感、作者性与类型创新,才真正开始变得清晰。
韩延的新跨度,从现实情绪到想象世界的触角延伸作为国内现实题材创作者中表达力最为突出的导演之一,韩延的创作可谓极具特色。他的现实线作品看似题材跨度巨大,但深层逻辑始终一致,而这一逻辑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生命三部曲”中,从《滚蛋吧!肿瘤君》到《送你一朵小红花》再到《我们一起摇太阳》,韩延不断在现实交叉处,寻找一种既诚实又温柔的叙事方式。
这一点在《肿瘤君》中已经可见雏形,在这部作品里,他通过漫画式跳切与幻想段落,让原本沉重的叙事获得了轻盈的亲近感,无论是熊顿挥剑斩向象征肿瘤的僵尸,还是将不苟言笑的梁医生幻想成韩剧男主角,她都用想象力为自己也为观众筑起了一道抵御恐惧的屏障;到了《送你一朵小红花》,它将痛感从个体命运扩展至家庭系统,疾病进而成为家庭成员之间重新理解彼此的关系联结,随着人物丰富起来,这套情绪方法论也走向更成熟的群像。
而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他更进一步,让两个被病痛判了“死缓”的年轻人相遇,凌敏与吕途的关系从各取所需的契约开始,在一次次斗嘴与陪伴中生长为超越生死的依恋,最终让生命万岁的主题在观众心中生长。这三部作品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递进脉络,从而完成了一次关于生命叙事的系统性探索。
在生命三部曲之外,韩延延展出一条更广阔的现实线。他在监制的《人生大事》中让殡葬行业伴随儿童寓言。在《我爱你!》里,他以素描式镜头处理老年爱情,常为戒和李慧如在游乐场坐旋转木马,两个满头白发的老人随着音乐轻轻起伏,从而让暮年的情绪变得克制而动人。这些作品背后的方法论始终统一,用关系替代命题、用情绪递进替代强制表达,从而让现实更为动人。这种方法论,是韩延打造自己作者风格的基础,也构成了观众对他的持续信任。

不过,如果只把韩延理解为现实主义导演,便容易忽视他创作体系中另一条被长期低估的支线——奇幻线。从《肿瘤君》中熊顿脑海的跳脱段落,到《动物世界》中完整的游戏机制与高概念视觉体系,再到短片《未来赞美诗》中对抽象科技与记忆空间的探索实验,他始终保持着对想象力、结构实验与视觉奇观的兴趣。只是过去十年的市场更需要他的现实线,使得他的奇幻能力一直处于被分散、未被大规模承载的状态。
但《星河入梦》的出现,正让两条路径在特效工业的加持下走向交叉。它既延续了韩延现实线中对人物情绪的精准理解,又让奇幻线的视觉野心得以完整释放。更关键的是,他选择的不是轻量级的软科幻,而是一种太空冒险式故事,这是一种对特效工业、叙事密度以及世界观搭建要求更高的方向,这种类型既需要导演有能力组织信息结构,又需要在风格繁复的体系中守住人物情绪的线索。巧合的是,这恰恰与韩延长年累积的能力高度契合。
在《星河入梦》中,韩延将十年的现实线经验迁移到一个更自由的叙事空间,正是这种轻盈科幻的选择,让它在市场中显得特立独行。从影片本体出发,《星河入梦》依然是今年春节档最值得讨论的作品之一,因为它不仅是韩延跨入科幻的首次大规模尝试,也是他过去十年现实线与奇幻线的一次同场;这既构成其创作路径上的阶段性跃迁,也是证明导演纵深能力的重要节点。

尽管《星河入梦》最先展露出的,是其天马行空的奇观设计,但影片真正的叙事核心依旧延续了韩延一贯的以人为本。影片将故事放在未来的太空航行中,人类已经能跨越星际,却仍需依赖“良梦系统”进入深度睡眠,以延缓衰老。当一艘飞船系统故障、船员集体被困梦境深处时,良梦管理员徐天彪与舰长李思蒙必须入梦排障、把所有人带回现实。
在这其中,人物的真实感来自两种气质,一种是行为气质,一种是语言气质。徐天彪从一开始就与AI互怼、嘴硬且松弛,李思蒙被唤醒后,两人的疲惫与吐槽交替出现,这种摆烂的状态,与当下年轻人的情绪极为贴近,也让影片的核心受众能即时代入。而李思蒙的山东话、徐天彪的四川话,是影片刻意保留的锚点——梦境空间可以无限跳脱,但方言能立刻把人物从光怪陆离的梦境里拉回真实,哪怕系统再怎么重置,只要两人对视和互呛,现实的紧迫也就及时回归。
另外,影片的核心卖点——多重梦境也绝非随意堆叠,而是一整套心理结构的外化。最先出现的考场梦,是所有年轻人共同的压力象征,这与他们的自我焦虑紧紧绑定。随后即是港风茶餐厅的无限流结构,这里看似是古惑仔式的轻松,却暗含着一种层层归零、不断重来的秩序焦虑,而工程师老白在这场梦境中变成一条无忧无虑的狗,也有着明显的讽刺意味:当现实逼迫你去“卷”,年轻人心里最想做的,其实是一种犬儒式的高高挂起。

随着故事深入,影片的反派葛洋以小丑的身份频繁出现,他在梦境中沉浸得越深,越显露出一种虚脱的荒诞。葛洋本质上不是恶,而是某种被时代推向极端的逃避者,他厌恶现实,却无力改变,于是企图在梦中扮演创世主,掌控一个只围绕自己旋转的世界。这种心态正是当代个体在巨大社会机器面前无力感的具象化,在现实无法掌控的前提下,人只能向虚拟世界索取一种虚假的主权。葛洋的梦境,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茧房,这也与当下沉迷短视频和虚拟世界的人群形成了对照。
这样多元的人物状态,也让良梦系统托举起另一层隐喻,当体验可以被生成、欲望可以被托管,人是否会逐渐失去对生活的主动选择?在这里,两位主角的对位变得耐人寻味。徐天彪的自嘲和轻松,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对被系统替代的潜意识不安。相反,李思蒙始终承担决策,她必须做选择、承担后果、确保所有人能醒来,她的现实感,是影片真正的支点。两人一轻一重,一松一紧,恰恰构成了人类面对技术失序时的两种基本姿态。
因此,《星河入梦》的轻盈从来不是浅表,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忧虑:如果连我们的遗憾与焦虑都能被系统打包成体验,人类究竟是在被疗愈,还是在缓慢放弃自我?影片在视觉狂欢后留下的,正是这种隐隐作痛的现实回声。
在宏大叙事之外,科幻如何变得可玩可感当我们把人物关系、叙事逻辑和当代焦虑都重新放回影片本体,再看《星河入梦》,就会发现它在国产科幻中的特殊性,其实并不止于梦境这个设定,而在于它对观看方式的重新探索。过去数年,国产科幻往往延续大命题驱动的传统,要么着力构建宏大叙事体系,要么强调沉重的价值命题,而《星河入梦》选择这种更轻盈的路径,是要让科幻从仰望星空,回到可玩可感。
这种可玩性被落实为一种具体的体感。不同于《2001太空漫游》或《流浪地球》以宏大、稳重、固定机位建立的肃穆感,《星河入梦》的镜头语言更像一台随时加速的游乐设施。韩延用快速推拉的镜头运动、节拍明确的动作编排,以及高密度的音画节奏叠加,把眩晕、失重、坠落、被抛出的瞬时感受直接施加到观众身上。比如徐天彪与李思蒙被卷入葛洋梦境、多层折叠空间的段落中,镜头以过载的加速度穿梭楼宇间;紧接着,两人又瞬间化为二维水墨动画角色,叙事视角也切换为平面动画,观众也得以拥有多样的梦境体验。
声音设计也承担着同等重要的沉浸任务。系统提示音的骤响、环境音的切断、音乐情绪在不同梦境之间的瞬时跃迁,都像在为每一次空间跳转敲下明确的节奏拍点。正是这种视听层面的精准组织,让观众的注意力形成一种被牵引的惯性。这种连续不断的视听巧思,让观众在影院里如同畅玩了一场“梦境过山车”。

很个性,对吧?这也就意味着,它是挑观众的。
也正因此,《星河入梦》在春节档的低迷表现,根本上并不是创作问题,而更多是语境问题与策略问题。影片偏年轻化的气质,天然更适合暑期档那类学生与年轻观众密集入场的时间窗口,高饱和多巴胺色彩、快节奏场景切换、拼贴式梦境与“0说教、0烦恼”的整体调性,本质上是为想看一场开脑洞的、欢脱气氛的电影的人所准备的。而春节档的观众结构更偏家庭场景,选择影片时往往以“全家观影”为首要考量,这类节奏跳、风格杂、氛围更接近年轻人审美的作品,天然不占便宜。
此外,关于演员层面的讨论,同样是这部影片绕不开的问题。片中表演层面出现的不适配,很大程度上是类型电影的要求与主要演员此前的表演经验之间存在着断层。以饰演徐天彪的王鹤棣为例,他过往主要活跃于古偶、青春言情与轻喜剧语境,如《苍兰诀》《大奉打更人》,所塑造的人物多依赖演员本人特有的少年感热血感推进,过往的表演对危机叙事与内心戏的要求并不高。《星河入梦》虽然看起来跳脱,但依然对表演层次提出了更复杂一些的要求,影片要求在极端设定中精准切换从戏谑到危机的多层表演节奏,以此在信息密度极高的视觉场面中保持人物线索完整,在缺乏经验的前提下,第一次挑战大银幕的演员显然无法准确去驾驭。尤其再叠加上春节档的这一档期选择,多部大片影帝影后、高国民度演员集体上阵对打,年轻经验不足、主打青春市场的演员结构更使得该片与他们自身都落入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
《星河入梦》票房表现受档期选择、演员阵容等多重因素影响,我们确实很为它感到可惜,可见在更加跌宕的电影市场,一部电影的市场成功需要更全面谨慎的布局与决策。
只是,《星河入梦》在国产科幻语境中的探索性,还是不应被遮蔽。影片已经证明,科幻不必依赖宏大叙事和沉重命题,也可以通过规则、风格与节奏的重新组织,有机会成长为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透过这次尝试,韩延导演或得以有信心把自己的作者风格迁移到更自由、更开放的结构里;影片本身开出的那条路径,也是《星河入梦》值得被记住的地方。